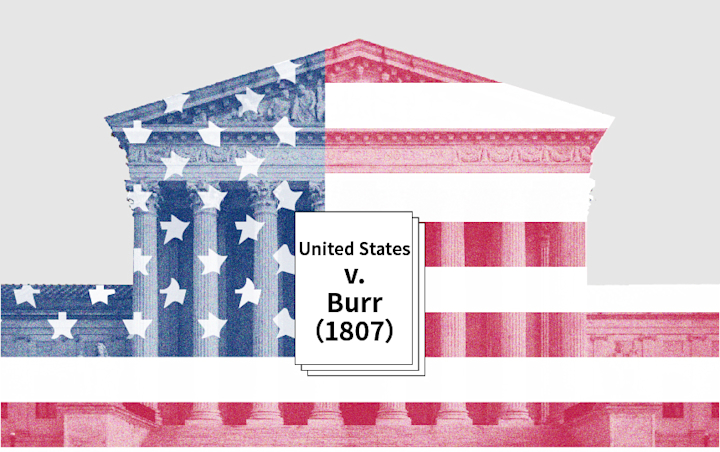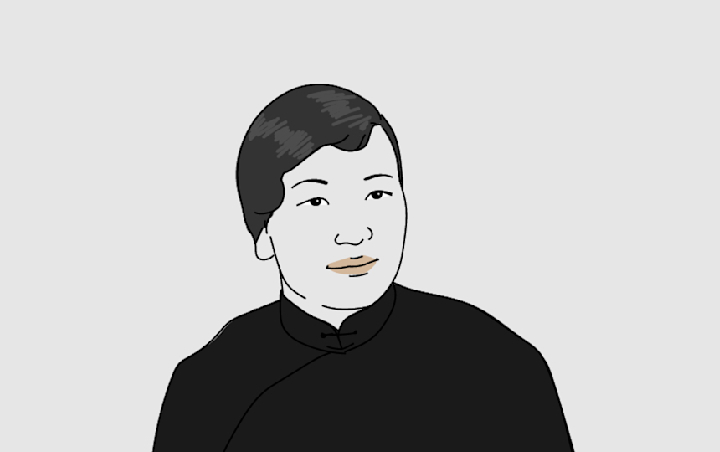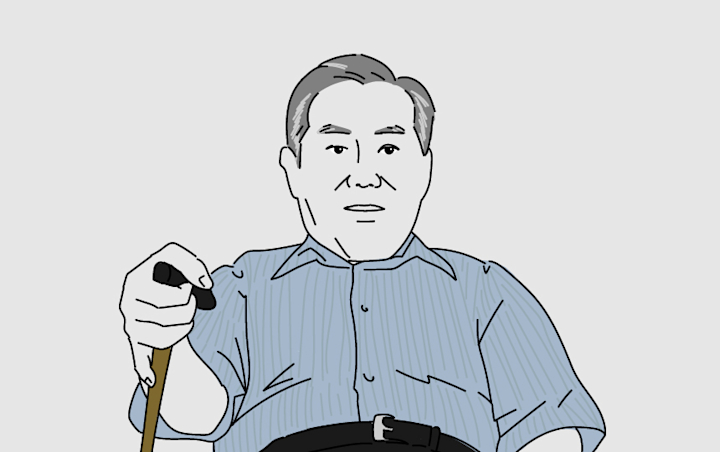臺灣商務印書館
2021-02-01發佈
2023-03-07更新
《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讓蔣介石玻璃心碎的胡適|話鹿讀冊

本文作者:潘光哲,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副所長。歷任國際日本文化研究「外國 …
《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讓蔣介石玻璃心碎的胡適|話鹿讀冊
本文作者:潘光哲,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副所長。歷任國際日本文化研究「外國人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等。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臺灣史。
著有《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等專書及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另主編《殷海光全集》(新版)、《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
玻璃心碎滿地:胡適和蔣介石「抬槓」之後
(摘自本書第一章第三節,頁37以下)
一九五八年回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和《自由中國》的實際負責人雷震,兩人固然關係密切,但彼此之間卻不是什麼事都「膩」在一起的朋友。舉例來說,中央研究院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舉行院士會議,非學界中人的雷震,當然不會是受邀的對象,無緣「恭逢其盛」。然而,長久以來出入宦場的雷震,自有提供消息情報的「眼線」。因此,胡適和蔣介石在這個場合裡公開「抬槓」的事情,雷震當天就知道了:
今日聞總統致辭,除稱讚胡先生的道德,並謂提倡固有文化和道德,以為反共復國之用,而胡先生的致詞,說明中央研究院工作,是為學術而研究,與道德毫不相干,雙方意見是大有出入,一說是針鋒相對,惟胡先生措辭甚為得體耳(雷震,「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日記」)。
雷震認為,胡適在這個場合裡對蔣介石的回應,「措辭甚為得體」;然按諸胡適的講話紀錄,未必如此。胡適當場就說蔣介石的講話「有錯誤」:
剛才總統對個人的看法有錯誤,至少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
爾後胡適將自己的講話紀錄,修改得比較溫和一些:
剛才總統對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
顯然,李亦園回憶,胡適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應該就是這段話稍帶點誇張意味的「口語版」。
這一席話聽在蔣介石的耳裡,當場應該不致於如呂實強的回憶那樣,「立即怫然變色,站起身來便要走」;證諸胡適與蔣介石等人步出會場的照片,彼此間好似還是言笑晏如。
但聽到胡適一席話的蔣介石,即便沒有當場「發飆」,心裡也實在「耿耿於懷」。勤寫日記的蔣介石,當天以氣憤之情躍然紙上的筆墨,回應了胡適:
雪恥: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辭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個妄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之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余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
朝課後,手擬講稿要旨,十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院長就職典禮致詞約半小時,聞胡答辭為憾,但對其仍以禮遇,不予計較。惟參加安陽文物之出品,甚為欣慰。午課後閱報,晡約請各國使節春季遊會二小時完,心神疲倦,入浴晚課,膳後車遊回寢,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安眠。
因著胡適的回應而「終日抑鬱」、必須得「服藥後方安眠」的蔣介石,第二天的腦海裡還是纏繞著這件事,揮之不去:
雪恥:昨日的沉痛成為今日的(安樂)自得認為平生無上的愉快,此乃犯而不校與愛人如己的實踐之效也。惟夜間仍須服藥而後睡著,可知此一刺激太深,仍不能澈底消除,甚恐驅入潛意識之中,故應以忠恕克己的仁愛之心,加以化冶,方是進步的勝利之道。今日讀《荒漠甘泉》「一個信徒能不動聲色地忍受苦痛,不僅是恩典,亦是榮耀」之語,更有所感。
胡適儼然成了蔣介石心底的一根刺,怎麼樣都讓他感到不舒服。兩人再見,胡適的一切言行舉止,蔣介石都可以挑出「毛病」: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貽琦等。
胡適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歡迎胡、梅同回國服務之語一出,胡顏色目光突變,測其意或以為不能將梅與彼並提也,可知其人之狹小妒嫉一至於此。今日甚覺其疑忌之態可慮,此或為余最近觀人之心理作用乎,但余對彼甚覺自然,而且與前無異也。
每個禮拜都會在《日記》裡留下反省紀錄的蔣介石,那一週最重要的省思,就是自己被胡適公開「抬槓」這件事了:
胡適就職典禮中,余在無意中提起其民國八、九年間彼所參加領導之新文化運動,特別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點,又將民國卅八、九年以後,共匪清算胡適之相比較,余實有尊重之意,而乃反促觸其怒(殊為可嘆),甚至在典禮中特提餘為錯誤者二次,余並不介意,但事後回憶,甚覺奇怪。又在星期六召宴席中,以胡與梅貽琦此次由美同機返國,余乃提起卅八年初將下野之前,特以專派飛機往北平接學者,惟有梅、胡二人同機來京,脫離北平危困,今日他二人又同機來臺,皆主持學術要務,引為欣幸之意。梅即答謝當時餘救他脫險盛情,否則亦如其他學者陷在北平,被匪奴��役而無復有今日,其人之辭,殊出至誠。胡則毫不在乎,並無表情。惟彼亦聞梅之所言耳,其心中是否醒悟一點,則不得而知矣。余總希其能領悟,而能為國效忠,合力反共也。
因胡適的言行,更使我想念蔡孑民先生道德學問,特別是他安祥雅逸、不與人爭的品性之可敬可慕也(《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十一,頁三六至三八)。
面對胡適的這番公開「抬槓」,蔣介石承受的心理創傷無以復加,自承是他自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與蘇聯派遣來的顧問鮑羅廷(Mikhail M. Borodin)發生正面衝突而「受辱」之後,「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橫逆之來」。回顧往昔,一九二七年初北伐軍事行動大有進展,攻佔武漢與南昌後,為了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究竟應該遷往南昌或武漢一事,蔣介石與鮑羅廷雙方激烈爭辯不已。一月十二日蔣赴武漢,當晚在武昌舉行的宴席上,鮑羅廷指責中國國民黨革命有摧毀農工之行為,「詆毀」國民黨領袖中央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張靜江,「指責」蔣介石「袒護黨中老朽,喪失革命精神」,「警告」蔣介石不得有反對共黨之舉動。鮑羅廷的批評「聲色俱厲」,使蔣介石難堪之至,當天日記裡,他這樣指陳自己的感受:
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華民族之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儘是賤辱而不可侮蔑也。
翌日一早,蔣介石仍感覺餘恥猶在,心恨未解,當天的日記紀錄曰:
昨晚憂患,終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幾欲自殺,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
他自稱:要到稍後會客之後,心緒始覺「稍平」。接著,十時蔣介石前往湖北省黨部演講〈加強黨的組訓與改善黨政關係〉,演講完畢,再前往漢口華商賽馬場出席歡迎群眾��大會,「到會者約十餘萬人,擁護之聲不絕於耳,踴躍之狀,未曾見也」,會中演講〈革命應依正路進行〉。他參加了這場群眾運動,即使感受很好,也不能減少他的心靈痛苦:
以民眾熱烈之狀,使憂患為之漸息,不能不再鼓勇氣,然而痛苦極矣。
即便欲鼓餘勇的蔣介石,對來自鮑羅廷的侮辱恥感,仍始終深銘在心。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蔣介石再度回想,又興起自殺的念頭,「一死以謝同胞」,更對國民黨接受蘇聯支持援助的決策悔悟不已,以為蘇聯的作為,與其他帝國主義帶來的壓迫侮辱沒有什麼兩樣:
余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為余辱國。今日情況,余惟有一死,以殉國難,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三民主義留精神,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深信其不誤,然而來華如鮑羅廷等最近之行動,徒使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與其主義完全相反,國人有知,應驅而逐之。︙︙蘇俄同志乎? 爾如誠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國際之信用破產,應急自悟,改正方法,不使恢復至帝國資本主義之道路,則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則,余雖一死,不足救國,且無以見已死同志於地下! 故余惟願我全國同胞速起,以圖獨立自主,不負總理三十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一,頁一三七、《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二,頁七至九)。
時空場域大有不同,蔣介石自己感受到的創傷,好似沒有什麼兩樣。他都有厚望於對方,反而在公開的場合裡,被當場「教訓」了一番;想要當場「翻臉」,勢有不能,只好藉著紙墨,發洩一肚子的怒氣。沒有來自蘇聯的支持援助,國民黨無法改組,蔣介石建軍黃埔,發動北伐,更�是「不可能的任務」。鮑羅廷呢,正像是這股助力的化身;還不是國民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勢難抗衡。而想要「反攻大陸」,一定得仰仗知識人群體的合力,胡適則是這個群體眾所矚望的最高代表;已經是至尊政治權威的蔣介石,面對「學統」領袖的挑戰,終究有所忌憚,不能頤指氣使。一句話,蔣介石非得公開忍辱負重不可。
個體的心靈創傷,會對一己的生命歷程帶來什麼樣漫無邊際的影響,而且反覆再生,揮之不去,沒有人知道。蔣介石對於胡適的負面觀感,持之如此,此後難免不能再私下壓抑,往往宣洩而出。例如,司法院副院長傅秉常聞人言,蔣介石在一九六○年十月五日國民黨中常會上公開批評胡適,說他到中研院後,對於「院士及博士之授予,均係以私人關係為主,所予者多屬不當」,還譴責陳誠「用胡之不當」。陳誠回敬說,任用胡適乃蔣「自己批准」。聞此言,蔣即「嚴詞」稱說:「研究院院長易人及推薦胡適之,既係行政院簽呈到總統府,『我如批不准,汝面子如何下去,我又不欲發生府院之爭』云云」。這番話,讓陳誠「幾不能下台」。蔣「罵興」既起,欲罷不能,復再「責胡等之利用美國人力量為不當」(《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頁四一三)。觀乎蔣介石當日日記的紀錄是:
上午主持值會,對所謂長期發展科學得經費其自私職勢之陰謀,久為學者所痛憤,而辭修推我的意思殊為駭異,當時行政院通過此案後報請我核奪,余即發還不批,只示其凡院會通過之案不應再請示批核,否則余乃該社行政違法之意,而其今日會中竟當面說謊,故不能不直說此案經過實情也,辭修虛偽不成蓋如此乎,可歎(蔣介石日記,抄件)。證諸蔣介石當日主持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四六次會議指示,其中之一為「長期科學發展計畫及此次由中央研究院辦理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事宜有未盡妥善之處,已交行政院檢討改進」(《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十一,頁三七九)。兩相比對,蔣介石批評的主題,應當是關於胡適主導下的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但無論是傅秉常聽到的話,抑或是蔣介石自己的紀錄,胡適都是蔣實難容忍,必須「開罵」的對象。
至於面對「雷震案」,胡、蔣立場根本「南轅北轍」。立意非讓雷震坐獄繫枷不可的蔣介石,自然聽不進胡適的意見。他批評胡適「實為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之曰『狐仙』,其乃危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彼尚不知其已為他人所鄙棄,而仍以民主自由來號召反對革命,破壞反共基地也」。胡適去世時,蔣介石親撰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自認對胡適「並未過獎,更無深貶之意也」。還洋洋得意地紀錄,認為這幅輓聯「自認為公平無私也」。當他公開出面弔唁胡適時,狀極哀慟,但當天的日記裡,對胡適卻是貶過於褒:
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民主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心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
乃至於蔣介石在三月三日留下的反省紀錄裡聲稱:「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十一,頁三八四、頁五三九至五四○、頁五四二)。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蔡元培百歲冥誕,中央研究院舉辦紀念活動,蔣介石親臨,認為中研院「環境污穢、設備零亂,毫無現代管理知識,殊為心痛」,他又將這筆帳算到已經去��世了好幾年的胡適身上:
此乃自胡適以至今日院長王世杰所謂新文化之成績也,所謂最高學府如此現狀, 何以立國與興學耶?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十二,頁四八五)
總言之,蔣介石日記裡對於和胡適的一切相關事務,統統沒有好話。
前去位於臺北南港的胡適墓園悼懷的朋友,一定都會看到蔣介石「智德兼隆」的題字;而蔣介石致贈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往往被人津津樂道。然而,蔣介石這幅輓聯,既深陷於將新、舊必可截然二分,不可調和的對立思維,也完全展現了他和胡適的思想世界距離多麼遙遠。胡適畢生不以三綱、五倫這種「舊道德」、「舊倫理」為然,焉可願為「楷模」或「師表」? 胡適的地位,怎麼會需要政治權威做出這樣的「蓋棺論定」呢。
知識人和政治權威之間的相衝突矛盾從來不曾停止,也不會停止。雙方之間相存共生的張力,緊繃難弛,卻往往以前者遭遇諸如「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劇為收場。胡適和蔣介石的公開「抬槓」,固然是知識人對政治權威懷持異議的展現;相對地,想鎮抑打壓而勢所不能的政治權威,最後只好訴諸筆墨,發怒洩恨。
約略同一時段,「君臨」中國的毛澤東號召知識人對共產黨提意見,結果竟是「引蛇出洞」的「陽謀」。一夕之間,以知識人為打擊對象的「反右運動」堂皇出世;影響所及,究竟多少知識人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至今還無定論。胡適當年如果決定留在中國,他的命運會是如何? 沒有人知道。這般知識人與政治權威之間的對決場景,卻值得我們再三沉吟。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