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珞亦
2020-03-02發佈
2023-03-02更新
最可怕的殺人法律,卻得到大法官的認可?|劉珞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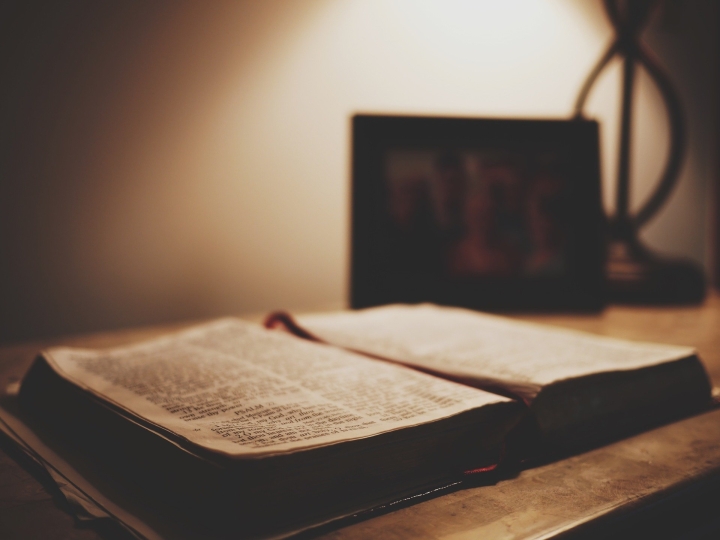
在《國際橋牌社》中,清大學生廖偉程因為讀了史明《台灣四百年史》,就被警察搜索宿舍,並且被帶到警局,一度被威脅要 …
最可怕的殺人法律,卻得到大法官的認可?|劉珞亦
在《國際橋牌社》中,清大學生廖偉程因為讀了史明《台灣四百年史》,就被警察搜索宿舍,並且被帶到警局,一度被威脅要以「二條一」來處以死刑。
而影片中一直不斷提到「二條一」,就是什麼?
是隨時要你死的「懲治叛亂條例」
在 1949 年時,政府頒布《懲治叛亂條例》,其中第 5 條這樣規定:「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就是說,你只被認定參加「叛亂組織」(像是讀書會),你就有可能被判無期徒刑。
這還不打緊,如果你又曾有「顛覆政府」的言行,你會直接適用當時最有名「二條一」,也就是《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犯刑法第100第1項、第101條第1項、第103條第1項、第104條第1項之罪者,處死刑。」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只要你犯了上述的罪,通通從本來的刑法規定改為「唯一死刑」。
好,那你可能會問?不是《刑法》有規定?為什麼犯了《刑法》的規定,又變成《懲治叛亂條例》?那是因為《刑法》是「普通法」,而《懲治叛亂條例》是「特別法」,而特別法優先適用。
所以假設你原本犯了刑法 100 條的規定,按照《刑法》當時的規定是:「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你有可能會被判7年以上,或是無期徒刑,但現在通通適用《懲治叛亂條例》就會變成「唯一死刑」。
在那樣的時代,你只要被政府抓到任何人民有「意圖」破壞或是顛覆政府,就可以被處以死刑。那怎麼樣算是「意圖」呢?例如參加讀書會,裡面讀一下政府不喜歡的書;或是在日記裡面被發現你對於社會主義是支持的;甚至你讀了裡面有台獨思想的歷史書。
因此,這個「二條一」就是台灣史上最惡名昭彰的法律。監察院曾經想要透過大法官解釋來挑戰,卻遭到難堪的失敗。
13歲參加的團體,卻是死刑的依據
想像一下,你現在是個13歲的少年A。
13歲,大約是國二的年紀,是一個你身旁朋友做什麼你也會跟著做的年紀。當身旁朋友流行玩戰鬥陀螺時,沒有戰鬥陀螺就是一件很遜的事情,當朋友都加入籃球隊或是棒球隊時,沒有參加一個社團就是一件很不潮的事。
所以當你13歲,看到你身旁朋友都加入某個團體時,一起加入就成為當時友情的一種「儀式」,哪怕那個「加入」,是未經思考的,甚至不是自己選擇的。
你能想像嗎?回到戒嚴時代,A可能就會因為 30 前曾加入某個兒童團,哪怕當年只有13歲,卻成為後來你被判死刑的依據。
大法官出手替威權助拳?
當時法院的 SOP 是這樣的,如果你被認定是「叛亂組織」的成員,又被抓到你有顛覆政府的「言行」(像是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就可以依《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判處死刑。
曾有一群像A一樣的 13 歲少年,在中國加入了所謂的「匪偽兒童團」,後來還是少年時就隨著中國國民黨逃亡來台,自然也無法繼續參與該組織的活動。
幾十年後,當初這些少年被認為是「共匪」,因為當時國防部認為,只要曾經參加過「匪偽兒童團」的人,反正他們都是共匪,都參與「叛亂組織」,應該要通通抓起來。但監察院覺得有問題,認為法律不能夠這樣用,因此向大法官求救,希望大法官好好解釋法律。
大法官作為民主的底線,本應就是要在各種國家機關違反憲法時,大聲的說出來,做憲法的守護者,保護人民不被國家侵害,維護自由民主的體制。
而這些戒嚴時代的「憲法守護者們」,在碰上這些法律問題時,是怎麼解釋法條的呢?
「懲治叛亂條例」是在少年們加入「匪偽兒童團」後才立的法律,刑法不是不處罰尚未立法的行為嗎?刑法不是不可以溯及既往嗎?
1956年,大法官們在釋字 68 號解釋說:「只要你沒有自首,或只要沒有證據顯示你沒有繼續參加,就當作你有繼續參加了喔!所以就算是法律後來才制定,但是你有『繼續』參加下去呀!所以你在修法之後,還是維持不法的狀態,這當然算是犯罪喔!」
釋字 68 號解釋:「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
刑法的使用,必須嚴守「無罪推定原則」,如果沒有事實顯示你有犯罪,就是無罪,但是1956年的九位大法官卻認為「只要你沒有證據顯示脫離叛亂組織」就說你有犯罪的意思。翻譯成白話文,只要你沒有辦法證明你沒有做,就是有做。
這個解釋在釋憲史上最為惡名昭彰,因為這種解釋方式根本就是「有罪推定」。
如果你是A,這時候你已經覺得很不爽了:「我要怎麼證明我沒參加叛亂組織?我就根本沒有參加啊?」(註:所以當時有不少被告在後來表示,自己從來都沒又參與,第一次參與叛亂組織就是在檢察官偵查的時候,因為�被威脅和刑求……)
好,沒關係,至少刑法有規定,未滿14歲的犯罪行為,不會成罪,就算我在13歲時參與所謂的叛亂組織,後來也沒有繼續參加,這樣我也不算犯罪吧!
這時,大法官們又做出另一個法律解釋。
少年們是13歲時參與「叛亂組織」的,後來也沒再參與,按照刑法的規定,應該不能處罰14歲以下的行為?
1970 年,大法官在釋字 129 號解釋中,這樣說:「我知道刑法有規定 14 歲以下不算犯罪,但你13歲加入叛亂組織,然後到了 14 歲,到了 15 歲,只要你沒有自首,沒有證據顯示你退出,你就算是有加入叛亂組織,就是有罪!」
因此這個可怕的規定就這樣一路來到 90 年代。
台灣人勇敢站出來反對
這個可怕的規定,就肆虐了台灣人好一陣子。直到發生了《國際橋牌社》中演的 1991 年「獨台會事件」,廖偉程等四位大學生被以「二條一」逮捕。
但當時,台灣已經出現變化,在 1990 年發生了野百合事件,台灣人在政治思想上已經出現質變,慢慢走向民主,所以這種迫害人民思想的法律,以及粗暴的獨裁行為,自然引起逐漸覺醒人民的反感。
因此開始有人大力批評政府的粗暴行為,並且在同年 5 月全國大學進行罷課,且在台北車站前進行靜坐的抗議活動。在這樣的壓力下,立法院在 5 月 27 日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並在同月 22 日由總統宣告廢止。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