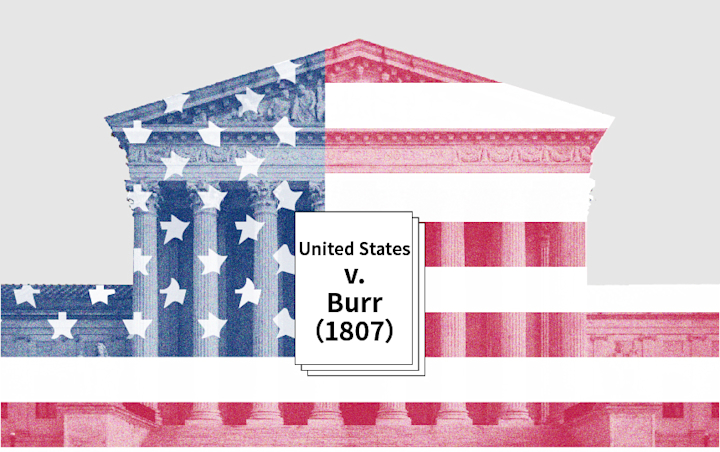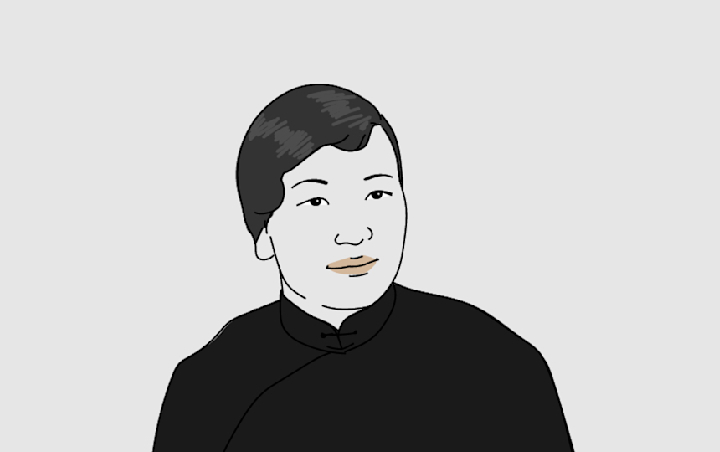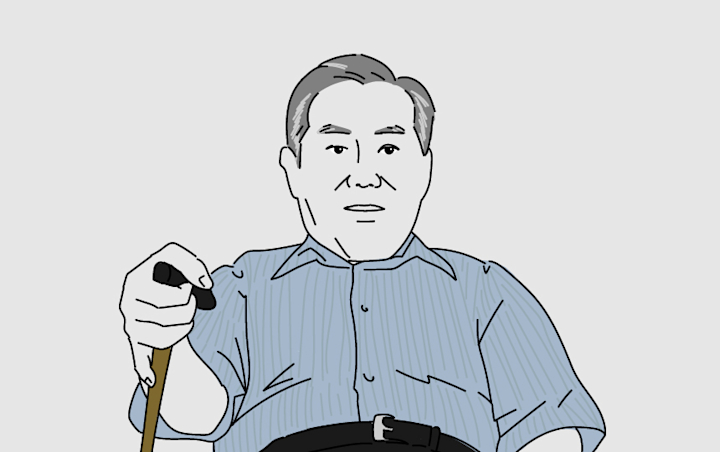臉譜出版
2018-03-31發佈
2023-03-25更新
《被誤解的犯罪學》書摘:你知道加強巡邏並不會減少犯罪率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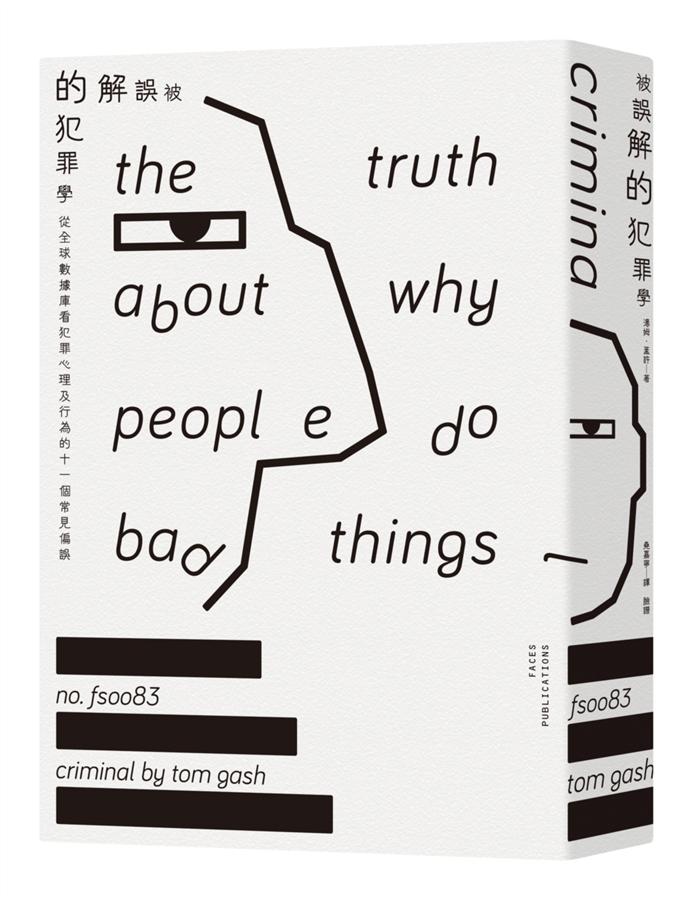
直探地下紐約、倫敦暴動、美墨邊境、各國監獄、大都會幫派及貧民窟治安等社會議題,以統計數字破解法律和道德間的迷思,並重新思考「人」為何犯罪?
奇怪的真實
佩特.梅休(Pat Mayhew)和她長期以來的合作夥伴羅恩.克拉克(Ron Clarke)把人生都投注在犯罪研究上。由於對犯罪方面的貢獻,他們在二○一五年獲頒斯德哥爾摩獎(Stockholm Prize)的犯罪學獎。當時我與佩特.梅休隔著一張桌子對坐,我問她如何與羅恩.克拉克一起發現了德國機車竊案的數量驟減。這問題有一部分就是在問她到底關注些什麼。她說:「我們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最常談論的,就是入室竊盜的案件和車輛的犯罪……因為車輛犯罪案件備受矚目,以至於我們必須隨時關注車輛犯罪的狀況。」
但是,有這項發現也是因為她一直相信統計的力量(更甚基於印象而作的推測)。梅休在英國內政部服務的三十年期間,花費了大部分精力在改善和監測犯罪模式,好�讓英國和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能對犯罪行為有更深入的理解。她在一九八一年與麥克.霍夫(Mike Hough,現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犯罪學教授)一起進行英國犯罪調查,該次調查引進了一個計算英國犯罪趨勢的新方式,不再根據警方所蒐集的數據(警方的數據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報案),而是出自一群數量龐大、經過仔細採樣的英國人口,由這群人回報意見(不對外公開)。在那前後,她也一直在整理犯罪資料,並定期檢討,上述資料除了英國之外,也包括全世界的。比如她便完成了對德國機車竊盜案的資料匯編。
她說:「我們與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undeskriminalamt)一個叫作埃德溫.庫別(Edwin Kube)的人聯絡上,我們發現德國人(不愧是德國人)手上有非常非常好的犯罪數據。」這對於梅休和其他參與共同研究的人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許多國家並沒有區分機車、汽車或是腳踏車的竊盜案數據。而且這個細部資料也顯示出,德國的機車竊盜案減少,跟德國整體犯罪趨勢不合。從一九八○年開始,有六年期間機車竊盜案掉了三分之二,不過汽車竊盜案的數量大致還是一樣的,甚至還略為上升,從一九八○年的六萬四千件,增加為一九八三年的八萬兩千件,而在一九八六年又跌回七萬件。
腳踏車竊盜案的數量大致穩定,也是類似的模式。德國人沒有突然變得比較守法,只是有些事就是不一樣了。
梅休說:「這還挺明顯的,不是嗎?」 我想:「或許對妳而言是吧。」
梅休還知道英國的機車竊盜案也在一九七三年突然銳減。荷蘭在一九七五年時也有類似情形。不過當我在戰略單位小組初次得知這個研究結果的時候,並無法對此現象有明確的解釋,而且它也大大�挑戰了我對於犯罪的成因和解決方式的某些偏見。
改變是起於歐洲國家意識到了道路交通的危險性。交通意外死亡率過高,主要歸因於車禍,同時人們也愈來愈同意要有預防措施,一方面保護自己的安全,一方面也要調控節節上升的意外相關醫療支出。英國在一九七三年規定騎乘機車必須要戴安全帽;接著在翌年,倫敦的機車竊盜案就減少了四分之一。荷蘭也在一九七五年規定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於是說自己曾經在過去一年碰到機車竊盜案 的人,突然從百分之十掉到約百分之六。德國的情況還更戲劇性。德國在不同階段引進了不同的法律,造成竊盜案減少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七月開始強制規定所有騎乘機車的人都要戴安全帽,幾乎就在同時,竊盜案的數量就慢慢在減少,在一九八○年則是急遽減少,因為政府規定(這項規定從該年開始實施)如果騎機車沒有戴安全帽,被抓到的話會當場罰款。
在這些統計數據的背後,代表的是數千人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道德選擇,儘管改變的原意並不是為了影響犯罪之類的。以前會偷機車的人現在不偷了,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沒有安全帽,他們被抓的機率將會大幅提高。有趣的是,根據比較仔細的德國資料顯示,這些人也沒有因此就決定去偷其他類型的車輛,藉以維持他們的興奮感,或是賺點外快。
為什麼我認為這個案例如此重要而它又如何引發了我的想像呢?它看起來與「英雄與壞人」觀點完全不符合,而這些現實生活中的罪犯到底又有多大的行惡決心呢?其實不需要多大的動員,就可以讓你在物色一輛無人看管的機車時,記得帶上一頂安全帽,不過看起來很多想要偷車的人都做不到。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得以問:我們需要竭盡全力將違法者定罪、施以處罰,才能夠減少�犯罪嗎?機車竊賊所受到的處罰並沒有改變,犯罪率下降並不是因為他們現在要被關的時間比較久了。真的需要全能英雄和十惡不赦的壞人對抗嗎?警察在犯罪事件的減少上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過有趣的是,他們通常不是透過戲劇性的追緝才達到這個目的,反而是因為日常執行一些「真正的」警務工作中所謂的「苦差事」,如此每天取締交通違規才達到的。
「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又如何呢?有人會假設,若社會條件沒有什麼巨大的改變,犯罪就不可能減少,但這個想法已經被推翻了。這幾年來,德國在福利制度或是財富分配上並沒有重大改變,然而我們卻不能忽略這段期間機車竊盜案減少了三分之二這個事實。即使這些犯罪者「是為了維持生計而被迫犯罪的」,但是他們也沒有增加其他型態的犯罪數,以彌補失去的犯罪所得。
雖然真實的世界複雜無比,但我們還是可以、也確實必須發展出新的思考方式,才能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行為中最糟糕的面向。所以我會利用本書,希望能夠說服你相信三個重要的事實。
1. 機會具有的力量
首先,光是思考人類的動機,其實不足以理解犯罪。你可能也發現了上述兩種關於犯罪的主要描述,都不脫這種嘗試。「英雄與壞人」觀點就只想要靠著加重刑罰,以威懾制止潛在的可能犯罪者。
而「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則想要藉著改善大多數弱勢者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例如提供工作或是更多福利就能消除他們違法的動機。如果能夠理解到底是什麼在驅使我們行動,這當然很重要,而且很令人心動。不過在現實世界中的我們,通常就是直接受到身邊環境的影響。二○一一年倫敦發生�暴動的時候,我住在倫敦東區一個靠近沙德韋爾(Shadwell)的地方。沙德韋爾是整個城市裡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它安靜的座落在城市邊緣,有許多中層的建築物散立於各處,其中的居民就是這次二○一一年倫敦暴動中的核心年輕族群。但是這裡沒有暴動。並不是所有貧窮、憤怒的年輕人都會發起暴動。幾乎所有受創嚴重的地區都有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商業區,這讓我在暴動當晚感到十分惱火,因為沙德韋爾幾乎完全沒有這些。或許是有些沙德韋爾人跑到別的地方去製造了事端,不過大部分沙德韋爾人並沒有額外去做這些,或說他們甚至不曾參與其中。
這就是我所謂機會的力量。我們一定都有一個所謂的臨界點,過了這個臨界點之後,我們就無法阻止自己做出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也就是說,我們所面臨的誘惑和挑釁,通常也和我們天生對守法的渴望一樣重要。其實,幾乎所有人都很容易墮落,我們尤其可以從倫敦暴動中看到很多這類的例子,在當時,一般正常守法的公民也跟著幫派分子一起搶劫,還有更令人煩惱的,是在歷史中某些醜陋的時刻,甚至還可能所有人聯手大屠殺。不過,比較正面的來看,即使是最反社會性格的人,也可能因為他們碰到的環境而完全被壓抑下去。單獨一人住在沙漠裡的殺人魔,不可能會犯下連續殺人案,就像是沒有車的鄉下盜賊,犯案次數一定比同樣住在城市裡的盜賊少。如果犯案的機會看起來很不顯著、或是很不吸引人,這極可能影響重大,上文的機車安全帽便是如此。
考慮機會的力量同時透露出另一種可能性,那也是我們很少考慮的。我們知道貧窮不一定會增加人們偷竊的動機(並因此導致犯罪),反而可能會因為值得偷的高價物品比較少,造成比較低的犯罪率。所以我們也可以��試著想想看:如果把兒童留在學校裡會減少他們觸法的機會,或許不只是因為他們受了教育之後有比較好的工作前景,也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受監督的時間減少了,比較難惹出麻煩。
我認為二十和二十一世紀所發生的犯罪率變化,最合理的解釋包括特定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的變遷,這些都足以徹底改變我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犯罪機會。我其實認為婦女解放一事,對搶劫的發生率不減反增;科技變遷是行凶搶劫增加的背後原因;而電動遊戲並沒有讓兒童沉迷於暴力,說不定還減少了青少年暴力。我也必須指出我們(為了保護人身和財產)的個人行徑,對於犯罪率的 影響力之巨大,並不亞於任何政府政策。
2. 理性的限制
第二點我想要說的是,在談到犯罪的時候,我們不應該過分高估邏輯的支配力。我們對於犯罪的兩種主要態度,背後都有一個共通的假設:人們會計算有多少誘因,並且會很快反應。「英雄與壞人」觀點認為只要我們讓犯罪無利可圖,就沒有人會犯罪了。而「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則主張只要我們讓多數人擁有穩定、有足夠吸引力的工作,就沒有什麼人會想要、或是需要犯罪了。兩者都借用了經濟學那看起來很吸引人的理性邏輯。
蓋瑞.貝克(Gary Becker)教授在一九九二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是他「將微觀經濟學的分析視野,拓展到非市場經濟領域的人類行為之中」。貝克領獎時,談到了他開始研究犯罪行為的決定性時刻:「我在一九六○年代開始思考犯罪的問題,開端是我有一次開車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一名作經濟理論的學生口試。當時我遲到了,所以我必須很快的決定是要把車停進停車場,還是冒 著被開罰單的危險,違規的把車停在路邊。我衡量了一下被開罰單的機率、罰金的金額,以及把車停進停車場的支出。最後,我覺得值得冒點險,於是就把車停在路邊了。(我沒有被開罰單。)因此我發現這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所以我開始比較有計畫性的投入這個領域。」
貝克最後達成的結論,在一九六八年首次出版,他認為犯罪者在本質上很像他。或者說——他在稍後又指出:「經濟學的方法認為人的行為都是出自理性,利益和成本決定了他們的行為,他們會衡量所有倫理和心靈等各個方面,再決定要採取什麼行動」。
貝克發表的論文和他的其他許多描述中都有一個潛在的假設,認為犯罪其實就是其他形式的工作的替代選項。貝克認為許多人之所以「成為犯罪者,是因為考量到犯罪(和合法工作相比)能夠獲得的金錢報償——他們也要考慮可能被逮捕和 被判罪,以及刑罰的嚴厲程度」。他切中要點的同時採用了「英雄與壞人」和「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因為「可以找到哪一種合法工作,以及法律、命令和刑罰,當然都是犯罪時要作的經濟考量的一部分」。他也同時採用了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方案,雖然相形之下比較強調後者。例如:他認為對初犯的寬大量刑,是在「鼓勵」青少年犯罪。
關於犯罪的成本和利益還有許多可以再商議的部分(尤其是對某些特定類型的犯罪),不過我認為如此關注動機,是過分誇大了我們能夠作出好選擇的能力。經濟學家的經驗法則是人們都會做出「有效的」決定,不過在此我想說的是,大部分犯罪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它們不管從哪一個面向來看,都稱不上是理性的。 如果我們從倫敦暴動中挑一些個案來看,儘管理性決定之下的搶劫是存在的,不過更��多的情況則是不那麼理性的例子。有一個青少年把他自己的照片貼在社交網站上,慶祝他第一次在特易購(Tesco)偷了一大袋印度香米。有無數暴民攻擊警察,也有數不清的人冒著被關的危險,偷了一些經濟價值極低的東西。二十三歲的尼可拉斯.羅賓森(Nicholas Robinson)從一家被洗劫一空的利多超市(Lidl)偷了六瓶礦泉水,這讓他聲名大噪(但是屬於奇怪的名聲)。他後來被判刑六個月,在宣告之前,他的律師告訴坎伯韋爾治安法院(Camberwell Magistrates Court)他「在當場就被抓了」,而且「羞得根本抬不起頭來」。
不只有犯罪(這種具有破壞性或是自我毀滅性的錯誤)才不總是理性的。在很多時候,犯罪才是「合理的」,但是人們卻選擇守法,這時候也可以看到理性的限制。想想有多少次,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違法。是理性讓你決定放棄這些機會嗎?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你根本沒有考慮過違法這個選項,而且,如果你決定做了違法的事,你會覺得這是不道德的行為,還會想自己竟為了利益而做出傷害別 人的事?
忽略了犯罪有不理性的面向——守法也是——讓我們過度把重點放在經濟上的利己主義,而忘了人們會選擇犯罪,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周遭的環境決定的,還有到底他們認為什麼是可以接受的行為,而什麼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可以先放棄人類是利己而且理性的假設,我們應該做的,是更進一步的釐清各種犯罪中究竟各有多少程度的理性計算。我們將在下文討論到,其實理性的方式可以阻止不理性的行為。我們也將會看到,讓某些族群更有能力抗拒不理性的誘惑,或許是一個有效減少犯罪的方式。
3. 小事情的妙用
��第三點,我希望大家注意到小事情的重要性。有兩件事可以說明這是對的。首先,一點小變化就可能有很大的效果。我們已經討論過如何改變一件事的結果,因為像是在西德,光是一個人如何衡量偷機車這件事,就可能對犯罪造成極大的影響。不過類似可以影響的事情還有很多。細節的影響之所以重大,其中也包括去理解人們在什麼時候最願意改變。舉例來說,我們知道當吸毒者的朋友剛發生藥劑過量的問題時,最容易說服他接受治療;或者囚犯剛出獄的第一週則最危險。
有些犯罪就像是會傳染一樣,以像是幾何級數的速度散播開來,直到開始減少,這似乎跟專研病毒爆發的研究會提出的模式很類似。與幫派有關的暴力犯罪最容易出現這種模式,一個非計畫中的意外事件,就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報復舉動,以牙還牙的行為也會逐漸升級。但是這也表示如果我們可以阻止一件類似的犯罪,就可以預防更多。這甚至可以適用於連續殺人案。雖然人們傾向於(毫無根據 的)認為殺人犯「天生就是殺人犯」,不過連續殺人犯幾乎大部分都是由意外事件造成的。像是亨利.李.盧卡斯(Henry Lee Lucas)、傑佛瑞.丹墨(Jeffrey Dahmer)和愛德蒙.肯培(Edmund Kemper)這些連續殺人犯第一次犯下謀殺時,都是因為承受了(各種不同的)極大壓力,然而接著,殺人或是逃過偵查的快感,讓他們在心理上感受到興奮,於是想要尋求下一次,接著就造成了悲劇性的結果。
李察.庫可林斯基(Richard Kuklinski)是一位美國職業殺手和連續殺人犯,被宣判了五起謀殺罪,但是他宣稱自己殺的人不下一百人,他用一種緩慢而平穩的語調,描述了他第一次殺人,聲音裡幾乎不帶任何情感。「我在酒吧裡和人起了爭執,然後就打起來了……我隨手抄起一�根撞球桿打他。大概打太多下了。他就死了……不過,連我自己都有點驚訝的是,我先是感到很難過,但是接著過了 一會兒,我開始有了其他別的感覺。我不再感到難過了。我是有難過,(但是)多少也有點滿心想著我殺了人……」小事情所誘發的行為,足以影響我們行事的可能性,並且讓我們重新形成自己的個性,在未來增加、或是減少我們犯罪的機會。
另一個說小事情有妙用的理由,是因為大變化可能會造成出乎意料與變化無常的結果。如果要解決的問題極為明確,但是我們的解決方案卻很粗略、只有大方向,那麼我們就必須極度小心。大膽的政策通常起不了什麼作用,這種例子不計其數,如:美國在一九六九年試著檢查所有通過墨西哥邊界的車子(不過這對於毒品交易沒有什麼影響,只是耽擱了合法的貿易活動);強制判決(Mandatory Sentencing)政策(這讓監獄中塞滿了低犯罪風險的囚犯);以及大型的都市再生計畫(這類計畫一直以為金碧輝煌的建築物就比較安全,但其實並不見得)。 重要的永遠是小事情,大型改革很少會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但是我們將會發現:其實大部分政府都很不理解、不知道怎麼處理這樣的世界。在過去的七年間,我在英國政府研究所工作,主持一些研究計畫,考察政府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我理解到在最佳的情況下,政府其實可以做得很好。不過我的研究成果也告訴我,如果我們是真心想要解決犯罪和其他複雜的社會問題,現在的政策制定和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都需要做一些改變。
話鹿讀冊,不定時跟您分享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