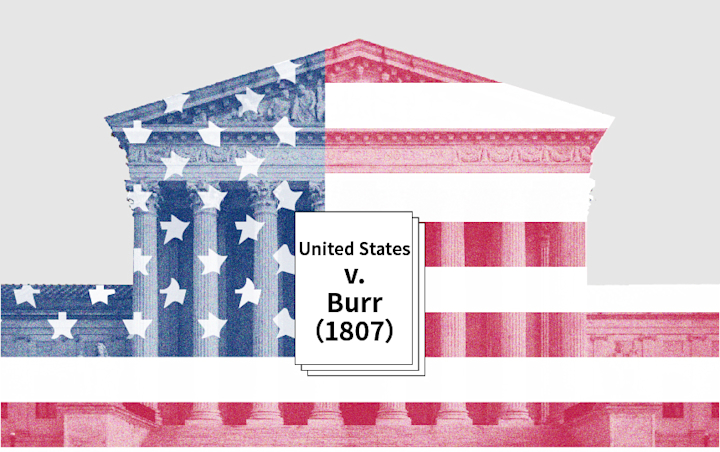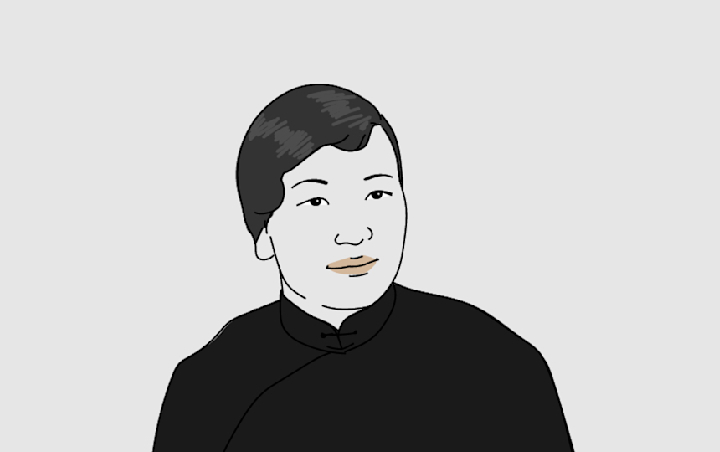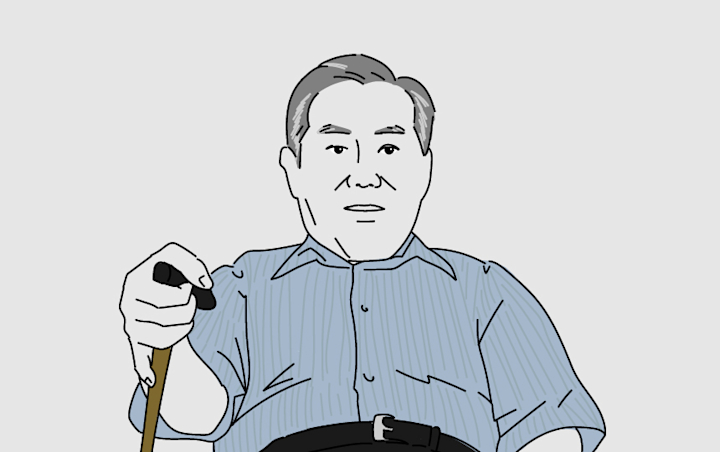光現出版
2018-07-03發佈
2023-03-07更新
《死刑肯定論》書摘:復仇,是野蠻還是偉大?

復仇是野蠻還是偉大? 根據柏拉圖的轉述,蘇格拉底認為「與其採取不正行為,不如接受不正行為」。 他並進一步使其普 …
《死刑肯定論》書摘:復仇,是野蠻還是偉大?
復仇是野蠻還是偉大?
根據柏拉圖的轉述,蘇格拉底認為「與其採取不正行為,不如接受不正行為」。
他並進一步使其普遍化,導出許多命題,諸如:「比起接受不正行為,人類更不認同施加不正行為。」「不正直者比正直者更不幸。」「不正者接受刑罰,比不接受刑罰更幸福。」
在這些刑罰思想當中,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並不認同復仇或報復。對於犯罪行為進行反射性或情感性的報復,並非人類真正該有的樣態(〈如野獸般莽撞復仇者〉柏拉圖《普羅塔哥拉篇》[Protagoras]),因此不僅排除被害人的私人復仇,從原理上來說也排除了國家代為執行的復仇。
對此,亞里斯多德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不同,他明白地承認復仇和報復是一種正義。
亞里斯多德認為:「報復者可以平息怒火。」「因為復仇更有人性。」「因為自己受害,以同樣方法還以顏色的人,(藉由復仇的過程)不太可能再有行惡事的念頭。」「人總期待能以惡制惡。如果不這麼做,便會被認為是奴隸的態度。」「以成比例的方式應報,可維持國家。」(《尼各馬可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
亞里斯多德主張,若以溫和的德行來控制怒氣,也要看時間和場合。假如受到不當的侮辱而不發怒,已經不叫溫和,而是膽小。正當的怒氣也是一種德行。這種時候因為怒氣而想要復仇,完全沒有任何該受責難之處。不僅如此,甚至稱得上是偉大的態度。
作為一種復仇替代品的死�刑
根本上要看採取何種哲學立場(這是和復仇觀念相關的「正義論」領域),假如以權力論來看,又會如何?
承認「作為替代被害人行使復仇權的死刑」這個立場,亦即承認作為主權權力之行使的死刑。這種情況下,國家作用的性質如同前述,以權力分析的觀點來說,牽涉到刑罰制度的源頭。國家實力的獨占,便是要求從其他主體回收實力的情況。同時,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復仇權的剝奪,其中產生一種權利的剝奪。也就是說,這只是一種權利剝奪的補償措施。
在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當中看不見權力的扭曲與狡獪。因為這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想法。事實上,國家從被害人手中拿走復仇權後,還認為國家可以不替代被害人行使復仇權,甚至完全不允許復仇權由國家代為行使,才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型態。
從權力論的角度看來,不如說死刑肯定論的想法較為中立。
由上述可知,「死刑=被害人的復仇權代行」這個立場,得以在無關意識型態下成立。透過權力分析的角度來看,也可說是一條確實的道路。這與討論正義論時前述的「蘇格拉底、柏拉圖vs.亞里斯多德」何者正確無關,而是要說亞里斯多德的正義論立場,也禁得起權力論的檢視。
當然,死刑不能光靠被害人情感成立。因為若是如此,就不需要有審判的量刑判斷。同時,在刑罰制度中也無法直接承認赤裸的復仇情感。這種情感必須昇華為共同體的「官方報復」。
而當尋求死刑的被害人情感獲得市民社會共感的支持時,復仇情感就會昇華為官方報復的死刑。尤其是像裁判員制度一般,經由市民代表的裁量所支持,復仇情感將會在社會中獲得承認、占有官方位置。再也沒有比此更高的「昇華」。
這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合意。
�也就是說,復仇原理可以成為死刑原理。正確來說,這是已經昇華為共同體中官方報復原理的被害人復仇情感之意念,並非復仇思想本身,同時復仇權代行被認可的範圍也大幅縮小,並無適當稱呼,因此以下僅稱「復仇原理」。
保護被害人的構圖
附帶一提,以上論述並非認為反對論無法成立。
在正義論中,站在前述蘇格拉底、柏拉圖流派的思想上,認為復仇情感除了昇華,也必須斬斷,為了復仇的代行而發動死刑,也可以認為是一種殘酷的主權權力行使。要站在這種正義論上進行價值判斷,提出非議也並非不可能。
然而,從權力論的角度來看卻會產生一個疑問:被害人的復仇權遭到扼殺的壓抑性該如何處理?
說得更明白些,復仇情感(不僅昇華)應該斬斷的想法,甚至可說是在另一種意義下帶著權力性。乍看之下,在企圖保全被告人生命這一點上,似乎與權力性無緣,其實在割捨被害人的復仇權時,就已經包含並非如此的一面。
死刑無疑是一種嚴酷實力的行使,但只要死刑和被害人的根源性尊嚴重疊,那麼,只因這是一種權力作用而批判發動該權力的行為,並沒有太大意義。更應該做的是,站在權力論的角度,思考為何國家可以單方面禁止被害人的復仇權,因為這無疑是對個人的壓抑。我們看不到任何根據支持國家權力可以不採取任何代行措施,強制禁止被害方進行復仇。
不承認死刑制度的想法,打從一開始就不承認所有復仇權的代行,因此站在完全不顧這些狀況的前提上。我不認為與公權力的關係上,被害人的復仇權可以被輕忽到這個地步。所以從權力論的構圖來看,否定死刑的立論──我們往往會直覺反對―反而包藏著問題,有其困難。此外,即使對復仇抱持否��定態度的蘇格拉底、柏拉圖流派思想,也絕對無法以與殺人的暴力衝動相等的意義,來說復仇觀念「野蠻」。
到頭來,承認作為一種復仇權代行的死刑,可連結到國民的權利觀念與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其中存在著必然性。
如同光市母女殺害事件[1]中,被害方「如果不判死刑,被害人(遺屬)將無法重新站起來」的呼籲獲得社會廣泛迴響,產生同調觀念時,作為一種主權權力的行使,死刑將得以成立。
支撐死刑的社會共感
那麼,接下來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要向國家要求執行代理被害人情感的死刑呢?到了這個層次,並沒有明確的指針。
只能依據每個人不同的接收方式、情感、主觀。不僅被害人情感會因人而異,第三者(構成社會的人)的接收方式也不可能完全一樣。
比方說,在光市母女殺害事件中,妻兒遭到入侵者殘忍殺害,假如兇手在殺害被害的妻子後即終止犯行,也就是被告並沒有進一步殺害嬰兒便離開,那會如何呢?依然會同意執行作為被害人情感代理的死刑,承認死的權力的行使嗎?
相反的,假如犯人不是十八歲的少年,而是成年人,那又如何?現實中對這個案子的死刑結論感到抗拒的人,在這個假設下或許會產生不同的想法。再進一步說,假如犯人是成年人,又是有過強姦等同類前科的累犯時,又如何呢?
到頭來,作為主權權力發動的死刑,其實就是定位、成立於如此不安定又模糊的市民情感之上。
反過來說,這正表示包括裁判員審判在內,市民之間的討論有多麼重要。
前面稍微提過,當求處死刑的被害人情感受到市民社會的共鳴所支持,復仇情感在社會中獲得承認,占有一席官方位置時,死刑將昇華為官方報復,也可以說,「共苦」觀念�就是死刑的分水嶺。
如同在第三章中所討論,如果將人類「共存在」的樣態(死刑制度為其可能性之原理)列為死刑制度的終極根據之一,在這裡也可以逆向檢視這個想法。人類「共存在」的樣態,以對他者的受難採取「共苦」的方式展現。「共苦」是將他者的痛苦內化,藉此,人類社會得以與單純的利益集團或者出於畜群本能的集合,做出明確區別。可以說是一種在最深處,令人類社會得以成立的本質規定。最後我們可以說,「共苦」正是死刑成立的核心。
忽視被害人情感的死刑
相反的,違背被害人情感的死刑又如何呢?
被害方(遺屬)明明不希望判處死刑,卻依然宣告死刑,這不可避免地必須接受權力論觀點的批判。
檢察官求處死刑的重大案件,而被害方並不希望判處死刑的案例,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可能例如弒親、全家自殺、親戚之間為了保險金而殺人等類型。在這些事件中的被害人遺屬,也同時是被告人的祖父母或者兄弟等近親。因此,被害人情感期待「不要判死刑」、「不希望求處死刑」,反而更為普遍。
然而,日本的死刑權力對於這類案例也會毫不顧慮地判處死刑:
-
- 弒親案(最高法院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判決)
- 全家自殺案(仙台高等法院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判決)
- 親戚間保險金殺人案(秋田地方法院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判決、長崎地方法院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判決)
這種死刑權力的行使,甚至忽視犯罪被害人(遺屬)的意志,只能說是一種權力的空轉。違反犯罪被害人(遺屬)的心情而奪取人命,究竟有什麼意義?這種情況下的「人命」,除了是被告人的生命之外,同時對遺屬來說也是另一個家人的生命。
在這當中,國家權力是在「暴力的獨占體」之上與市民社會對立的存在,可以說是一個超越了利維坦的超級怪物。
從權力論的角度來看,(從死刑肯定論的立場也一樣)這是一個必須徹底批判的現象。
當然,弒親、親戚間保險金殺人,不能免於遭到強烈的道德責難。不過也不能因此將單純的道德論和法律、思想、哲學、社會學等見解混為一談。假如在此混為一談、輕易肯定死刑,這種人也難以免於「被死刑權力奴役」的汙名。
被害人情感被迫讓步的情況
無論被害人情感有多麼殷切,有時也會面臨被迫讓步的情況。
例如,當犯罪結果悲慘至極,即使被害人情感極為渴望求處死刑,市民或市民社會卻無法同意、同調的情形。這種情況,通常是犯罪背景牽涉到社會結構的扭曲,或者階級間的摩擦、經濟格差等廣義的社會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看來可以說是因為社會的扭曲導致該犯罪現象的發生。面對由此產生的現象,是否該以死刑來終結問題,則是社會整體必須面對的問題。
比方說,在日本審判史上有一樁名為「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殺人事件」的著名案件。一名精神科患者遷怒於過去的主治醫師,在堂堂白晝下持利器到醫師家,殺害醫師一家(妻子與母親)。
這個事件在社會上引發極大迴響,檢察官當然希望求處死刑,然而法院卻沒有認可,因此演變為從昭和後期[2]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左右,訴訟持續將近二十年的大事件(東京地方法院八王子支部一九九三年七月七日判決、東京高等法院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一日判決、最高法院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六日判決,結論皆為無期徒刑),這樁命案也牽涉到當時精神醫學界的混亂。
主治醫師曾對犯人施以前額葉白質切除術這種精神外科手術,犯人對此不滿,因而動手殺人。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是切除患者部分大腦的手術,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或許覺得詭異可疑,但是對於有爆發性粗暴傾向的精神病患者,確實具有戲劇性的鎮定效果,因此有一段時期被視為劃時代的新療法,席捲了精神醫學界。創始者安東尼奧.埃加斯.莫尼斯(António Egas Moniz)也因此功績榮獲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
發明前額葉白質切除術的莫尼斯是葡萄牙神經學、精神醫學權威,他精彩的生平事蹟令人瞠目,除了是醫學家,也是活躍於國際舞臺的外交官、政治家,不僅留名於醫學史,更在現代政治史中占一要角。
莫尼斯從學生時代即投身政治運動,關注的範圍很早就超越單純的醫學領域,出類拔萃的優秀讓他年紀輕輕便獲任命為科英布拉大學醫學部教授,但他並不以此滿足,後來跨足政界,在四十多歲時擔任外交官與外交部部長,是歐洲社交界深受歡迎且赫赫有名的名士,還曾與知名電影女演員傳出緋聞,留下許多顯赫功績與光鮮亮麗的生活經歷。在上述活動之餘,他的研究還榮獲諾貝爾獎。
而莫尼斯所創始的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或許可說帶著些許炫目榮光的殘影。之後,前額葉白質切除術這種醫療行為本身的有效性受到質疑,再加上副作用嚴重(弱智、喪失精神衝動、形同廢人等),後來基於人道觀點遭到禁止。
令人深思死刑意義的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殺人事件
在這種精神醫學的國際潮流轉變中,日本發生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殺人事件。
事件名稱衝擊性十足,犯下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殺人的被告,說得好聽,是個具備超乎尋常堅定意志的人,說白了就是性情�激烈的人。
被告出於家庭經濟因素只上到中學,不過靠著自學學習英文,成為口譯,智力極為優秀。另外少年時,也曾在拳擊比賽的縣大賽上優勝,體力體能相當優異。
被告除了口譯工作之外,進一步立下志願成為作家。由於在美國職業摔角界有門路,他試著寫體育報導到專業雜誌去毛遂自薦,後來文章開始刊載於一般雜誌和報紙上,作家身分受到肯定,稱得上是現在運動寫手的先驅。當時,在這個領域與被告同受注目的還有梶原一騎(高森朝雄),之後梶原一騎創造出《巨人之星》《明日的丈》等故事,獲得少年們狂熱的歡迎。相對照之下,被告的人生則跌入谷底。
他因為細故和親戚(妹妹夫婦)起了爭端,被告向來不懂妥協的性格讓事件發展到上警局。後來他遭到羈留,但是在警署不斷吵鬧,主張自己不該受到拘留,後來檢察官判斷他需要強制住院。強制住院的精神病院診斷被告為具有明顯爆發傾向的精神病患,執行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手術(當中之一種腦扣帶回切除術)。
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是切開頭蓋骨的開頭外科手術,因此需要取得患者的同意。被告在取得親戚同意下進行手術。
接受前額葉白質切除術後,被告無法像以往一樣撰寫文章,出現經濟危機,生活漸漸困苦。他認為一切都要歸咎於讓自己動了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手術的醫師,長年積怨,最後終於決定殺害醫師。他查出醫師位於東京都小平市的住處,前往該住處,但並沒有殺害醫師,反而以利刃慘殺醫師的妻子與母親,並且搶奪財物企圖逃亡。
當天,該醫師因為參加同事的送別會,深夜才回家。回家後,看到妻子和母親的屍骸倒臥在已成血海的自家客廳。
對被害人醫師來說,這無疑是一場噩夢,這起犯行所造成的傷害只能說是悲��劇般深刻又悲慘。
儘管後來前額葉白質切除術遭到全面禁止,不過當時仍是一種正當的醫療手段。例如日本醫科大學等,許多大學教授和開業醫師都曾經對多數患者執行這項手術。因此,動了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手術的醫師並沒有任何過失,這樣的犯行只能說是一種遷怒行為。
然而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得不避免死刑的一面。
作為一種主權權力行使的死刑,替代被害人的復仇權而執行。首先,被害人情感殷切,傷痛難以平息;其次,大家認為「此事切身相關」,在市民和市民社會中起了同調觀念時,死刑方可成立。不過犯罪背景潛伏著社會問題時,第二點便成為一個問題。市民和市民社會該不該與被害人情感同調,不得不令人存疑。儘管站在被害人立場,確實難以平息傷痛,但是對於抱持著扭曲結構的社會而言,則又另當別論。這時,如果單純與希望求處死刑的被害人情感同調,整個社會將會出現更大的矛盾。
許多犯罪現象都帶有脫離正常社會結構、社會功能的意義;反之,因為社會功能不全而產生的犯罪也確實存在。以後者來說,假如以死刑來終結,只會讓社會的功能不全更加擴大而已。站在社會性觀點來看,不得不抑止死刑,其結果只能迫使被害人的復仇權之代行讓步。
上述的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是當時轟動全世界的一大事件,此事還有後話。前額葉白質切除術的創始人安東尼奧.埃加斯.莫尼斯也遭到患者攻擊,因而半身不遂,晚年得靠輪椅行動。
[1] 光市母女殺害事件:一九九九年山口縣光市一個十八歲少年(日本國民滿二十歲才成年)闖入民宅殺害一對母女,母親死後遭姦屍。被告人一審與二審被判無期徒刑,但因未成年,服刑良好可能出獄;被害人丈�夫對此非常憤怒,持續上訴,至三審宣判死刑定讞。
[2] 昭和年代自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至昭和六十四年(一九八九年)。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