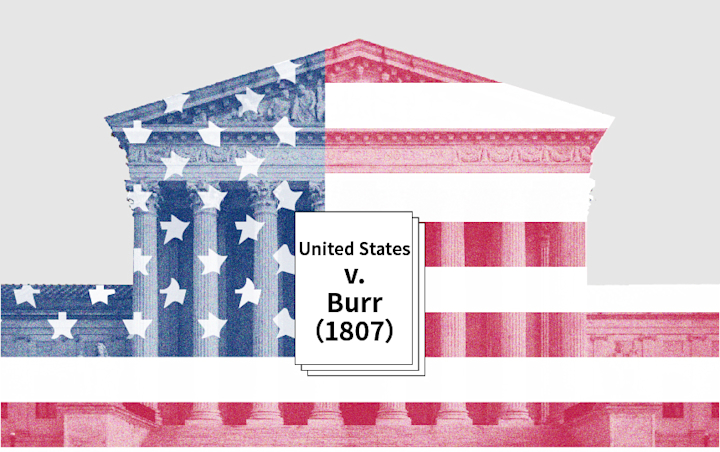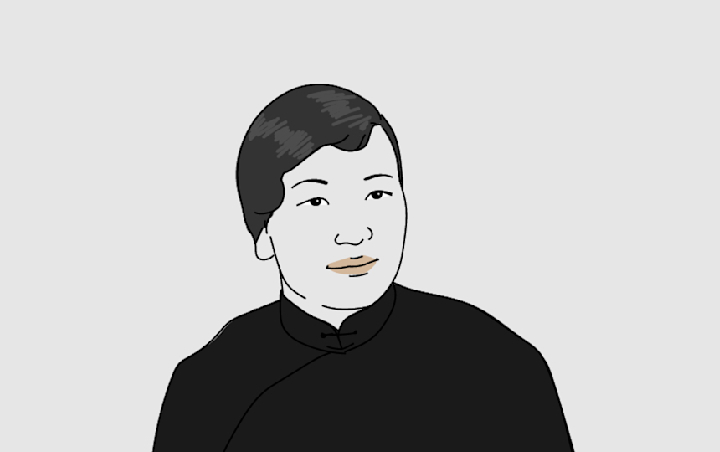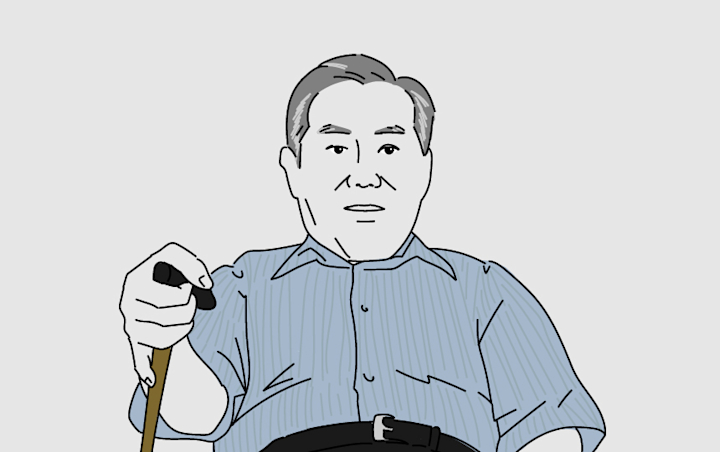李柏翰
2017-04-11發佈
2023-03-05更新
人權不是特權:「反毒戰爭」的健康權爭議|李柏翰

已經有許多證據顯示,客觀的教育宣導遠比嚇阻手段有效。訴諸道德情感從來都無法真正緩解各國政府與社會「想像中」的毒品問題;與其過分渲染恐慌,不如理性看待不同用藥者的需求與處境,及其背後的結構成因──比如失學者、無家可歸者、曾遭身心創傷者、家庭破碎或遭受家暴者、家中有其他物質依賴或濫用問題者,或因社交需求而接觸藥物者等。
人權不是特權:「反毒戰爭」的健康權爭議|李柏翰
台灣的國際人權公約第二次報告審查會議於年初落幕,專家委員會提出許多了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其中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10條的「監禁狀況中的人權」,委員們建議「放寬嚴苛的施用毒品政策」;[1]然而,法務部與司法院對這個問題仍然態度勉強,尤其法務部認為「 毒品罪 再犯率高」且「將毒品犯放出恐也危害社會治安,因此萬萬不可」。[2]
這個情況顯現了一件事:在台灣,關於用藥者(或一般人稱吸毒者)人權侵害的想像,似乎僅止於「監獄狀況」的考量。這似乎有些過時了。在國際社會中,目前關於用藥者人權的討論,更多聚焦在個人健康權的問題──重點不該只是「怎麼處罰才符合人權標準」,而是「處罰與否」本身就是一個人權問題。可惜,不管是國家報告、民間影子報告,或是專家委員會的建議中,關於健康權的討論,用藥者的處境連個影兒都沒有。[3]
聯合國健康權特別報告員Dainius Pūras在2016年關於青少年健康問題的報告中,建議各國尋求懲罰性或壓制性毒品政策的替代方案;且在進行相關爭議的國際談判時,應以個人的健康權為主要考量。先前針對2016年4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關於毒品問題特別會(UN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Session on drugs),Dainius Pūras就曾強烈抨擊:不分青紅皂白地將用藥者一律打成罪犯,將違反國家保護個人健康權的法律義務。
事實上,這不是人權專家第一次��有人從「健康權」的角度關注毒品議題,諸如前聯合國秘書長Kofi Annan和前任健康權報告員Anand Grover都算是先驅者。後者早在2010年的報告中,就已經深入檢討過國際毒品管控體系對健康權的影響,當時他也建議各國「建立一個類似《菸草控制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的形式,以取代懲罰性措施的毒品管制手段」。
卸任後,Anand Grover也加入了全球藥物政策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的倡議,該組織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推廣「以實證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管制與減害政策。其在每份報告中都苦口婆心呼籲各國政府以藥物管制取代用藥者處罰──即對事不對人!最近2016年的《推展藥物政策改革:除罪化的新方法》報告中,全球藥政委員會特別申明:
對於藥物交易的基層人員,包括供應、運送及種植者,必須實施替代性措施,因為他們大多是非暴力、僅為改善經濟的,因此對他們施以嚴懲是不正義的,而且也只會加劇他們的脆弱性。
在這麼長的引言後,本文想藉由上述的幾份報告,來談談為什麼傳統的懲罰性措施可能侵害用藥者的健康權,並引薦一下所謂「健康權的方法」(right to health approach)是如何看待毒品問題的──簡單來說,就是健康權對所有「用藥/吸毒」和「對藥物/毒品有依賴的人」仍都適用,不管是否有在用藥;因此,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或精神狀況不該影響他享有所有人權的機會。
「無毒世界」目標的盲點
不把「用藥/吸毒」和「對藥物/毒品有依��賴的人」混為一談是其中的關鍵!依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後者指的是一種會不斷復發的慢性機能失調,涉及大腦功能的改變,因此可能需要醫療手段的干預。然而,「用藥/吸毒」這個行為本身並不是一種病,並不等同於對毒品產生依賴;事實上,大部分的用藥者對藥物並沒有產生依賴性,不需要治療。
然而,目前國際反毒多邊控管體系所採用的手段仍然傾向認為:無論如何,用藥就是邪惡的(或不負責任,或不健康),因此國際社會有「無差別打擊」的道德與法律義務,也才需要「反毒戰爭」。以「戰爭」作為一種譬喻,正是為了合理化「零容忍」的態度與相應的極端手段。然而,這種作法非但未能實現「無毒世界」(drug-free world)公開聲稱的目標──防止毒品損害每個人的健康──也並未真正打擊到毒品生產與需求。
嚴懲無助「醫療模式」
透過刑事處罰阻止個人吸毒(行為犯)通常不會區別「用藥者」與「對藥物依賴的人」,也因此不可能細緻地分辨不同人的不同情況,而這也是為什麼再犯率只會有增無減。雖然吸毒的確可能對健康產生有害影響,但必須留意的是,現行的緝毒方式所造成的危害已經大於它要防止的危害──其所造成的「社會恐慌」等副作用不僅不符合比例原則,反倒還惡化用藥者的處境,讓他們不敢尋求協助、斷絕社會連結、抗拒健康干預等。
將吸毒視為犯罪,因而無法管控藥物的成份,卻也增加了吸毒者因「物質成份改變」所面臨的健康風險。比如2009至2010年間,在蘇格蘭發生用藥者因海洛因受到污染,發生了數十起炭疽桿菌感染的病例。儘管這種情況並不常見,但也突顯了毒品完全不受管制而可能造成其他健康傷害的可能性。然而,政府和社會大眾因「戰爭」的想像,普遍不在乎用藥者的健康損害。
但!並不是把所有用藥者都抓去「強制治療」就是好的。反之,對健康權最嚴重的侵害,通常就是在這種「懲戒性治療」的過程中發生的。比如在治療過程中受到醫護人員和其他病患的歧視或排擠、吸毒者受到強迫勞役等不知所以的處置,甚至被迫接受沒有實證根據的試驗性療法,卻又沒有獲得足夠且必要的資訊──換句話說,用藥者一旦被丟去治療,他們對醫療手段的「知情同意權」多半被完全漠視。
很多國家的毒品政策都先把用藥者描述成社會米蟲或道德敗壞者,再進一步否定他們具有「知情同意」的能力,但這根本不正當。從人權的角度來看,若當事人真的已經產生理性判斷的障礙,國家該做的應該是提供適當的輔助機制以消除決策上的困難,而非直接剝奪他瞭解、參與並同意治療方法與過程的權利。這點,正是所有現行毒品政策最欠缺的考量,不論是「嚴懲」或「減害」的制度皆然。
帝王條款:不歧視原則
關於毒品政策改革的討論,很多時候都容易陷入「吸毒要嘛很可惡,要嘛很可憐」的辯論,但重點並不在此。根據《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盟約》,關鍵在於國家是否符合它的立即義務(immediate obligations),包括「任何人不受歧視地享有各項人權」。如果政府為一般社會大眾提供許多具有實證基礎、重視醫病關係、避免傷害風險的健康服務,那麼針對用藥者的不正當差別待遇就構成歧視。
此外,「吸毒除罪化」並不等同於「用藥合法化」,這件事已經被宣導了好幾次,但仍有許多人刻意混淆其差別。除罪化可能有兩種作法:「不視為犯罪」(decriminalisation)或「除去懲罰」(de-penalisation)。前者是指完全排除刑法適用(但可能須受行政處罰),而後者是指解除懲罰(即雖然相關行為仍然是刑事罪,但只被處以微罪而取消監禁等);至於「合法化」(legalisation)則是不禁止相關行為。
無論改革與修法方向如何,政府都有立即對執法及醫護人員進行人權教育的義務,以減少因執法過當或醫療歧視所造成的恐懼和羞辱。與此同時,各級政府都應該開始考慮其他替代方案,如菸害防制是可能可以參考的模式之一,包括以科學方法評估各種藥物對個人和公眾的影響分別為何,以及每種藥物受到管制後對公共健康與人權的影響,並將它們逐一列入受管制清單。
又,菸草控制模式中的非價格措施也可能可以取代現有的執法框架──包括成分及含量規定、藥物教育與戒斷措施,以及透過提供未經摻雜的藥物以降低個人使用的健康風險或危害。此外,應特別允許有傳統文化用途的藥物使用(如玻利維亞的古柯葉和印度的大麻),不僅因為它們已被證實這類用途對公共健康影響不大,且無差別的「禁種」手段也剝奪了數百萬人的謀生手段。
要談人權,請來真的!
針對最一開始提到的聯合國毒品問題特別會,當時經過各國政府磋商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在會前草擬了一份會議結論,馬上引來同屬聯合國的人權專家們聯名公開的批評:雖然草稿中使用了許多「跟人權有關的語言」,但根本沒有充分指出國家的法律義務,也沿用「無毒世界」這個充滿傷害且落後的概念,�對於改革國際毒品控管制度根本無濟於事。[4]
儘管各國已經浪費太多公共資源在沒什麼效果的執法上,政府們卻仍舊傾向維持當今國際藥物法中的懲罰性措施,而這些措施顯然會有害於人權保障,尤其世界上甚至還有32個國家還保有毒品罪的死刑(每年約有1000人被執刑)。這些措施不僅造成刑事司法與監獄系統過度的負擔,也使得受刑人的處遇和生活環境非常惡劣(毒品犯更經常受到檢警的非人道待遇),政府也不太在乎他們是否能回歸社會。
由人權的角度出發,兒童、青少年及其他弱勢族群的用藥問題應該受到特別重視──不是要政府猛抓,而是要更加留意他們的權利侵害──不只因為他們的健康權本來就經常遭到漠視,再加上毒品產業鏈每個環節上的嚴刑峻罰,只會讓他們更加不受保護。因此,「防止接觸毒品」不能成為不合理侵犯青少年及其他弱勢族群權利的理由,包括隱私權、人身安全、受教權等,以及上述提到關於醫療行為的知情同意權。
結論
已經有許多證據顯示,客觀的教育宣導遠比嚇阻手段有效。訴諸道德情感從來都無法真正緩解各國政府與社會「想像中」的毒品問題;與其過分渲染恐慌,不如理性看待不同用藥者的需求與處境,及其背後的結構成因──比如失學者、無家可歸者、曾遭身心創傷者、家庭破碎或遭受家暴者、家中有其他物質依賴或濫用問題者,或因社交需求而接觸藥物者等。
各種情況所造成的個人脆弱性並不全然相同;而健康權特別報告員也曾特別提醒:相對於兒童和成年人,不被完全視為弱小而需保護的人,但也還不被法律承認是完全行為能力人的青少年,通常獲得的照顧最有限,可偏偏他們通常是最容易受到藥物引誘或影響的族群。要適當對付毒品問�題,應該採用「以健康權為核心」的觀點,來思考更有效且以人為本的策略,以確保「反毒戰爭」中的敵人是毒而不是人。
已經被批評到體無完膚的國際藥物法,目前正在著手修正與改良,而其實聯合國人權系統的態度轉變,也能從官方文件中drug的翻譯嗅出端倪──從早期的「毒品」到近期的「藥物」──就是希望透過「去汙名」作為理解與保障的第一步,以實現「人權並非少數人特權」的普世性。國際社會也正積極倡議各國提供可負擔且品質穩定的健康服務,包括基礎藥品、安寧療護、用藥資訊、減害措施等;於此之際,台灣準備好了嗎?
延伸閱讀
Acacia Shields (2009), The Effect of Drug User Registration Laws on People’s Rights and Health: Key Findings from Russia, Georgia, and Ukraine (New York: Open Society Institute)
Louisa Degenhart, et al. (2008), “Toward a global view of alcohol, tobacco, cannabis and cocaine use: findings from the 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PLOS Medicine, vol. 5(7)
Patrick Gallahue (2010), “Targeted Killing of Drug Lords: Traffickers as Members of Armed Opposition Groups and/or Direct Participants in Hostilities”,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Drug Policy, vol. 1, pp. 15-34
Ricky Bluthenthal et al. (1999), “Collateral damage in the war on drugs: HIV risk behaviours among injection drug us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vol. 10(1), pp. 25-38
Robert MacCoun & Peter Reuter (2001), Drug War Heresies: Learning from Other Vices, Times, and Pla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ssell Viner, et al. (2012), “Adolescence and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Lancet, vol. 379 (9826), pp. 1641-1652.
WHO (2009), Assessment of compulsory treatment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in Cambodia, China, Malaysia, and Viet Nam: An application of selected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 參見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66段。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初次審查時也曾被提及,因此這已經是專家們第二次建議政府鬆綁毒品政策了。參見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60段。
[2] 參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民間影子報告:回應兩公約 81 點總結意見》,第7段。
[3] 參見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46-51段。
[4] 最後特別會通過的成果文件《我們對有效處理和應對世界毒品問題的共同承諾》(A/RES/S-30/1)有稍微改進了,但仍未符合當時人權專家的期待。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