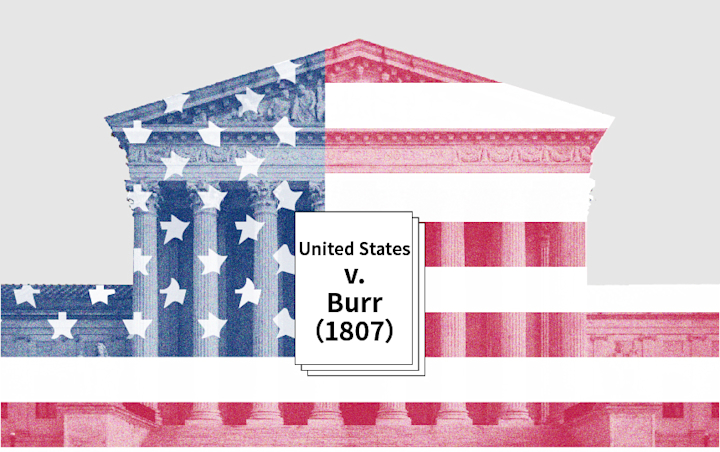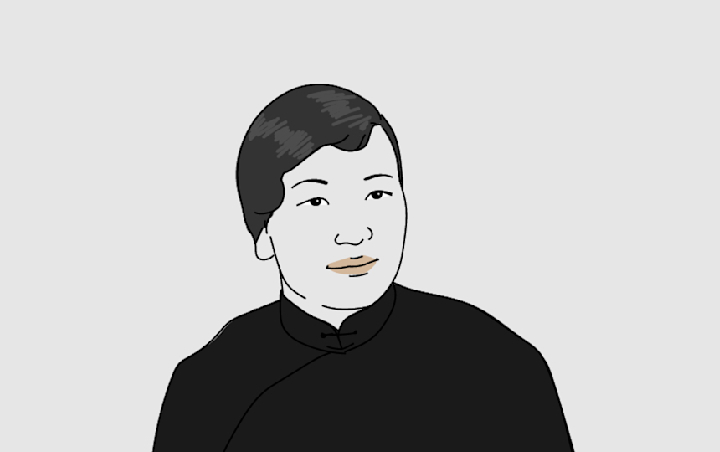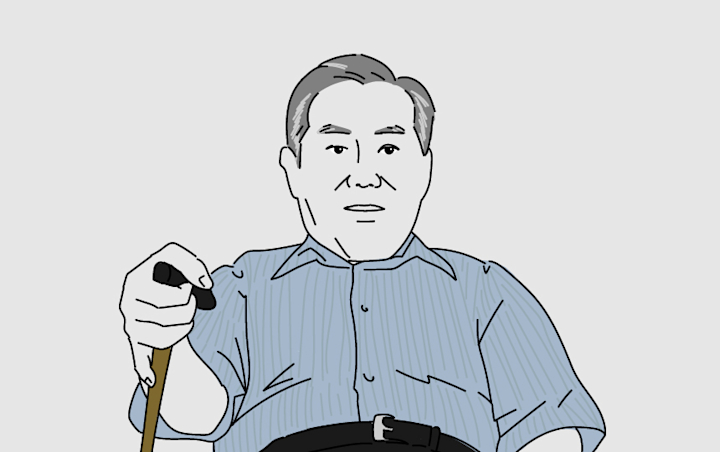蔡岳倫
2021-11-02發佈
2024-06-20更新
讓你說的母語,也成為你的國語|蔡岳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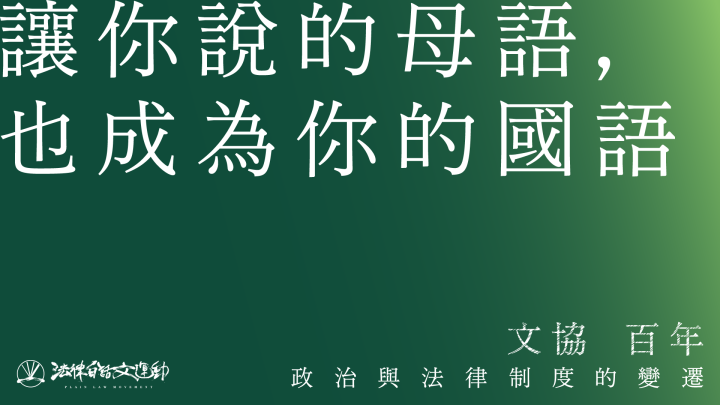
母語變成國語後,對於各種不同的國語間,是否應存在差別待遇、對於特定國語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是否反而壓抑了語言的發展,從日治時期到民主化後,都屬於我們需要一直面對的課題。
電影《異星入境》優雅地介紹了沙皮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該假說認為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形塑、甚至是侷限了我們的思考模式。語言對我們究竟有無如此深遠、根本的影響,或值商榷,但語言確實將我們腦海中的抽象思緒化為聲音,像在忙碌的上班途中想要買一杯冰美式,也須仰賴語言為我們傳意。
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使用、講述的語言種類,除了是自我認同的展現外,也是作為區分自我與他者的重要因素。
蔡培火與台灣白話字運動
一個民族所使用的語言、這個民族內會使用的語言種類為何,能夠召喚民族內的成員去想像這個民族共同體的邊界。雖然世上仍有多數民族並非僅同時使用單一種類的語言,但若統治者有意導入截然不同的官方語言取代該民族原有的任何語言,即有可能消滅這個民族原有的自我認同,進而使該民族成員難以回想原有的共同體界線究竟為何[1]。
日治時期時,日本政府對台灣採取漸進的同化政策,要求台灣人學習日語,在求學、洽公乃至參與國家公開場合,多需使用日語,也讓日語幾乎變成當時台灣人提升社會地位的道路上不得不學習的語言,也讓日語與其他日治時期存在於台灣的語言間,實質上確實出現差別待遇。
台灣文化協會的先賢蔡培火,在日治時期便致力於白話字普及運動(按:指台語的文字化)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希望藉此��達到逐步促成台灣人民整體素質進步向上以及民族自決等目標。
但嗣後蔡培火因外力壓迫而認為兩者僅得取其一進行推廣時,仍認為台灣白話字的普及為台灣進步之首要條件,不可半途棄之。
觀諸蔡培火一生投注於台灣白話字的歷程,早於13、14歲(約1914、1915年)時,從兄長處習得基督教會於台灣傳教的工具「羅馬式拼音台灣白話字」後,發現羅馬式白話字與兄長書信往來溝通無礙,往後就主張應藉由白話字的普及來增進台灣人的全體智識 [2]。
於1921年後數年,台灣文化協會曾決議以羅馬式白話字之普及做為業務的一部分,而蔡培火於1923年秋天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繼任台灣文化協會專務理事,其遂將普及羅馬式白話字與編輯白話字圖書等事項列入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工作項目。
1924到1925年間,台灣文化協會更曾數度舉辦羅馬式白話字講習會,也嘗試向總督府申請許可。然而總督府認為推廣羅馬式白話字,與日本政府所採取的日語推廣政策意旨相違背,更可能有害於日語的推廣,所以並未答應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白話字相關活動。到了1929年間,蔡培火與台灣文化協會對於羅馬式白話字所舉辦的講習會,都持續遭日本政府百般阻撓,蔡培火開始認為以羅馬式拼音推廣台灣白話字窒礙難行,好像該要另尋蹊徑了。
到了1931年,蔡培火開始以日文五十音創造「假名式白話字」,希望這樣能不再受到日本政府的阻撓,並多次前往東京尋求有力日本人的支持。返台後的「假名式白話字」推廣運動,仍遭到總督府反��對,在日治期間,蔡培火所致力推廣之白話字運動普及,終究未獲成果[3]。
台灣白話字運動雖然因為日本政府的打壓、運動能量的分散(當時另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閩南語本身各地口音的差異,造成羅馬式拼音、假名式拼音無法適用於全數的閩南語使用者等因素,而造成此運動的頹敗。
在白話字運動的目的,或許是不甘於未能受日文教育的台灣民眾,因為文盲者較多,進而沒有了自我增進智識的能力,所以在學習白話字後,台灣民眾能夠更迅速的獲取知識,最後達到廣泛、普遍提升台灣人學養的目的。
在這之中,更隱含想要抵抗日本同化、保留台灣文化的思想,同時亦顯露了部分語言平等的精神。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語言平等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都在2009年3月31日經立法院以條約案之方式審議通過,並於同年12月10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
語言平等為公政公約重要精神之一,其內涵應包括不得以語言做為差別待遇之根據、國家應保障任何人以任何語言傳述思想或出版刊物,以及國家應保存少數團體所使用之固有語言等,從公政公約中,關於語言的相關規定即可明瞭。
像公政公約第2條第1項、第4條第2項、第27條的下列規定,都可以看出保障語言平等的色彩:「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如經當局正式宣布緊急狀態,危及國本,本公約締約國得在此種危急情勢絕對必要之限度內,採取措施,減免履行其依本公約所負之義務,但此種措施不得牴觸其依國際法所負之其他義務,亦不得引起純粹以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階級為根據之歧視。」、「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有學者歸納出,國家於通過公政公約、經社文公約後,至少應負擔五種類型的國家義務。
首要者當然是國家本身不能侵害人權;次者即為國家應建立人權保障的核心機制,以積極保障人權,特別是於兩公約所保障的人權受到侵害時,國家應提供有效救濟的途徑;第三則是避免人權受到侵害的義務,除國家不應使其本身的機關侵害人權以外,國家更應特別避免私人間的權利侵害,此應透過積極立法及政策措施以達成;第四,國家負有提供基礎服務及設施以滿足基本人權之義務,國家於編列預算及政策分配上,必須將人民的生存權、健康權、居住權、教育權等基本人權做為施政之目標;最後則是,國家具有提倡人權的義務,如於各級學校推廣包含女性、兒童及其他弱勢團體之人權教育均係國家應推行之目標[3]。
而兩公約施行法其中第4條、第5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時,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兩公約規定事項;如果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應協調連繫辦理,而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等,都被認定是將前面的國家義務在法律上明文化,使國家對於實現公政公約的內容上,受到更明確的拘束[4]。」國家既然有積極透過立法以達成兩公約所保障基本人權的義務,則如果當前語言平等的保障未盡完備,就應該透過立法、修法而我國在2018年12月25日制定了國家語言發展法,並在2019年1月9日公布,嗣於2020年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其中《作為簽約國報告組成部分的核心文件》,亦載明「常用語言以國語(華語)最為普遍,我國過去因一言化的語言政策影響,造成部分族群語言流失問題日益嚴重,為保存及復振臺灣各族群語言及臺灣手語,2017年至2019年陸續制(修)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客家基本法及國家語言發展法,賦予各族群語言及臺灣手語平等之法律地位。」
從前面的報告內容中,可以看出國家語言發展法確實是國家為促進公政公約中的語言平等,而盡其國家義務後的成果。
金曲獎與《國家語言發展法》
從國家語言發展法及其施行細則本身的法條觀之,其實國家語言發展法既未明定何種語言為「國家語言」,亦未規定各種「國家語言」之正式名稱,法規本身僅泛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究竟何種語言屬於國家語言,仍是有爭議的。
於法規中不明定各國家語言的正式名稱,主管機關表示是因為「尊重各族群語言使用者慣常使用之命名權,不宜以法令規範各國家語言名稱」;而就國家語言實際上包含的語言,以一般社會大眾普遍認知而言,應至少包含國語(或稱華語)、台語(或稱閩南語、河洛語)、客語、以及各原住民族之語言,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客家基本法》亦已明定客語與原住民族各語言為國家語言,因此國家語言發展法主要補充者,應係台語之國家語言定位。至於是否有其他語言亦屬於國家語言,尚待釐清。
而從行政院的新聞稿來看,國家語言的範疇包含閩南語(分為南部腔、北部腔、內埔腔,海口腔4大腔調)、客語(包含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與詔安腔等5種腔調,另有主張四縣腔宜細分南四縣腔、北四縣腔,總共6種腔調者),而原住民族部分則包含阿美族、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邵族、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噶瑪蘭族、雅美族(達悟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16族42種語言別,或許可初步作為國家語言種類的參考範圍。
隨著新住民在我國人口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新住民母國的語言是否屬國家語言也引發討論。目前文化部對此持否定見解,認為新住民語言屬於移民語言,與法規文字本身「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之定義有別。
但若未來新住民於我國紮根時日甚久,而達到「固有族群」的程度(本文認為固有族群在解釋上,應從寬認定,較能廣泛保障語言之平等),是否新住民所使用的語言即會成為「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也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為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施行,我國各固有族群所使用之語言均屬「國家語言」,包含台語、客語與原住民族各語言均為「國語」,因此於2021年的金曲獎,將「國語」相關獎項均改為「華語」,而首度出現「最佳華語女歌手獎」、「最佳華語男歌手獎」等獎項,此處可見語言平等的實踐已不僅是國民基本教育的教科書而已,更躍然於通俗的日常生活間。
雖然國家語言的名稱、國家語言的種類不易釐清,法規本身似非毫無改進之處,但國家語言發展法確實課予國家相當的義務,包含:政府應定期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擬訂各國家語言之標準化書寫系統;優先推動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的傳承與復振措施;建構國家語言調查機制及資料庫;保障學齡前國家語言學習機會;規劃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之國家語言課程及學習資源;確保國民於參與行政、立法及司法程序時,得使用其選擇之國家語言;於必要時提供各國家語言間之通譯服務;保障國家語言之傳播權。
由於國家語言發展法之施行時日未久,亦非全部條文均已施行,目前國家語言發展法所課予國家的義務,對於面臨傳承危境的語言有無更進一步的助益,尤應觀察。
目前除新住民外,大部分人所講述的母語,於法律上確實已然成為「國語」,而在語言的傳承危機上有所依傍,得部分仰賴國家對於語言的推展與保存。
但於2007年獲得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的金曲歌手林生祥,於當年度即拒絕領獎,並認為音樂獎項不應以語言的不同為區�隔,若僅以客語相關獎項頒獎,則客語的創作仍然難進入主流的視野,此一質問迄今仍係鏗鏘在耳。
在將母語變成國語後,對於各種不同的國語間,是否應存在差別待遇、對於特定國語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是否反而壓抑了語言的發展,都屬於我們需要面對的課題。
[1]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時報文化,初版,1999年4月。
[2] 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著,自立晚報,初版,1987年。
[3] 陳玟錚,蔡培火及其政治文化抗日運動,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1月。
[4] 王自雄,人權兩公約之國內法化暨其施行法之實施─從國際法的內化與人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之法律地位論起,台灣法學雜誌,第164期,113-122頁,2010年11月。
[5] 張文貞,兩公約實施兩週年的檢討:以司法實踐為核心,思與言:社會與人文科
學期刊,第50卷第4期,7-43頁,2012年12月。
本策展「文協百年」,一起回顧那個年代,那些人們自覺與逐夢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