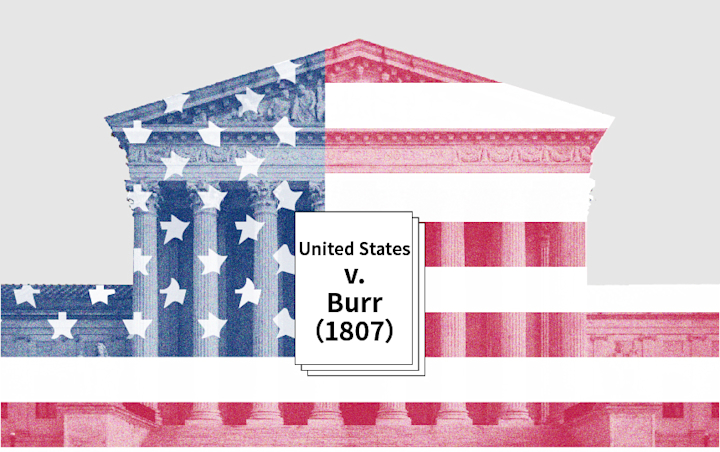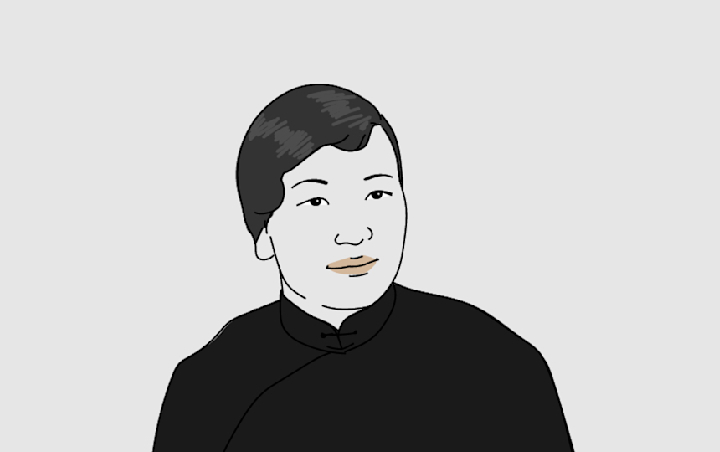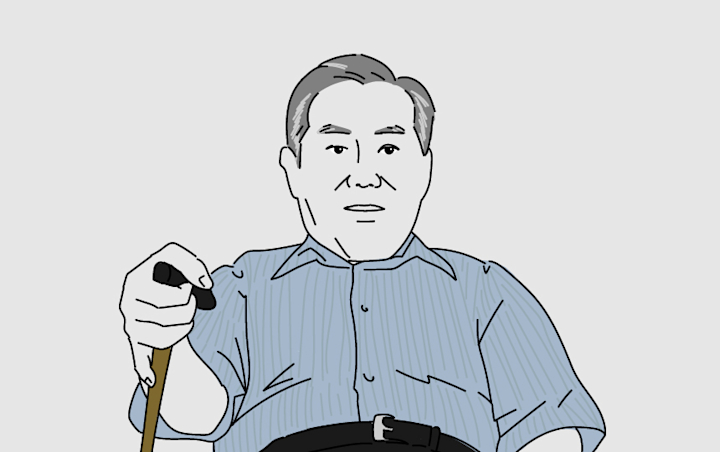黃郁真
2020-06-23發佈
2023-03-01更新
在《爭論中的德國》看見差異也看見共容|黃郁真

這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 2020的我們很忙碌,忙著接收最新的消息,忙著消化每則訊息,忙著處理隨之而來 …
在《爭論中的德國》看見差異也看見共容|黃郁真
這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
2020的我們很忙碌,忙著接收最新的消息,忙著消化每則訊息,忙著處理隨之而來的情緒。舊的議題還未獲得定論,新的議題就馬上被推到風口浪尖上,追逐共識的腳步遠遠趕不上相互碰撞的速度,就好像在對我們說:「抱歉,但你們無能為力。」
前陣子宣判無罪的台鐵殺警案在台灣社會掀起了滔天巨浪,有好多情緒在翻滾,憤怒、憎恨、失望、委屈……。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在大聲說話,希望自己被別人聽見,但也因為音量過於刺耳,大家紛紛摀起耳朵,最後彼此誰也聽不見誰的聲音。
這是台灣的日常,也是德國的日常
這樣的場景不只發生在台灣,一個被認為擁有成熟民主與理性公民的國家——德國,也始終走在這樣的不和諧與分裂當中。它是個複雜的國家,有著複雜的歷史、國情及人種組成,它歷經兩次的世界大戰失敗,用最民主的方式親手選出他們的獨裁元首,背負著納粹的原罪,更面臨種族主義、移民融合、難民問題、性別平等、環保政策等棘手議題的挑戰,這條路從來都不好走。
這個國家的勇氣,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二戰後的德國可以說是一片荒蕪,因此採取經濟優先的政策,加上當時美國與蘇聯成為對立的兩大國,美國為了要拉攏歐洲制衡蘇聯,必須先協助西歐各國進行重建而有了「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納粹問題在當時就被擱置了下來,在各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且曾經是納粹一份子的人,也因為政府在經濟復甦的過程中需要其協助而未遭到懲罰。
直到一位檢察總長——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於1960年代起訴了納粹相關罪刑,德國才開始正式面對納粹歷史。兩德統一後的首位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更在二戰結束40年,也就是1985年時發表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演講,改變了德國的命運。(演講內容詳見《爭論中的德國》)
觀察德國,反思台灣
2016年,全球有6000萬人因飢荒或戰爭成為難民,當中有許多人因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接納決定而來到德國。
事實上,這不是德國第一次對難民伸出援手,多數的德國人是接受難民的。然而,安置能力與輔導社工不足、文化融合、難民性別比失衡(男性居多)影響治安等情形,確實成為令德國政府頭痛的問題,少數難民所製造的性侵、暴力案件也引發德國人對難民政策的質疑甚至憤怒。民眾認為政府只知道當「濫好人」,德國社會陷入分裂,梅克爾則因為難民政策喪失選票,更面臨從政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
「如果光看這些數字,很容易無感,可是這些難民不是數字,多是如你我一般的常人,如果具體地將他們的生命史攤開來,旁觀的我們將被其中的巨大苦痛深深撼動。」這是一段很沉重的文字,但也提醒了筆者,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香港民眾提出來台避難以前,自己從未關注過我國的《難民法》草案,也未曾想過台灣可能碰到難民問題,在本書的閱讀經驗中,經常會有這樣停下來思考的機會。
「真理會在爭論中誕生。」(Die Wahrheit wird im Streit geboren.)
《爭論中的德國》一書是作者蔡慶樺對於德國社會�深刻的觀察。他從德國的爭論文化切入,用淺白的文字及輕鬆流暢的口吻,拋出一個又一個在德國社會中極具爭議性的議題——除了梳理背後的脈絡,還會有條理地將不同立場的論理交代清楚,就像在聽一位長年居住於德國的朋友講述他的人生見聞及獨到見解,讓你在佩服他的同時又會不斷被觸發思考。
讀完《爭論中的德國》後你會發現,書中所提及的議題幾乎都尚未獲得解決或達成共識,大家仍舊意見分歧、爭論不休,就像有著多元價值觀的台灣社會一樣。
但,「異中求同是求同一嗎?」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
筆者認為不是,也做不到,異中求同應該是:即便知道我們的立場可能不一致,卻還是願意先試著理解對方,一起辯論,雖然不同,但仍然可以共容。不可否認的是,爭論的過程的確會產生社會的分裂與仇恨,所以學習如何在爭論時變得更溫柔一點,放低音量打開耳朵,理直而氣不壯,筆者認為是很重要的,與大家共勉之。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