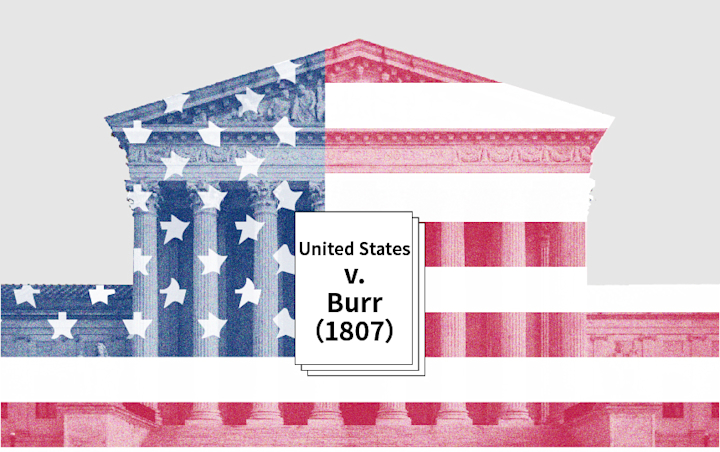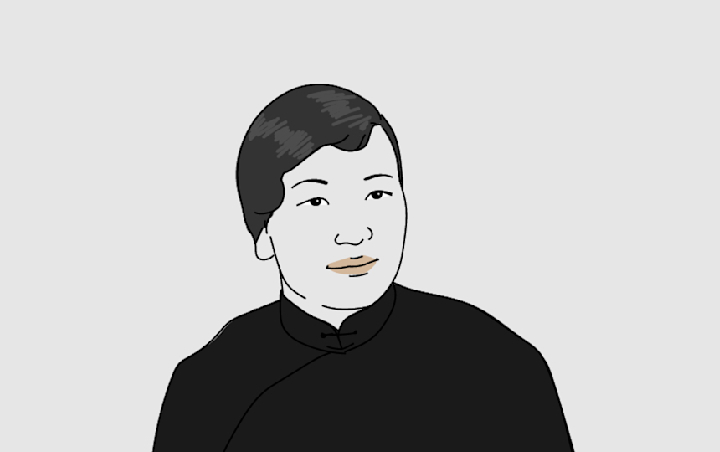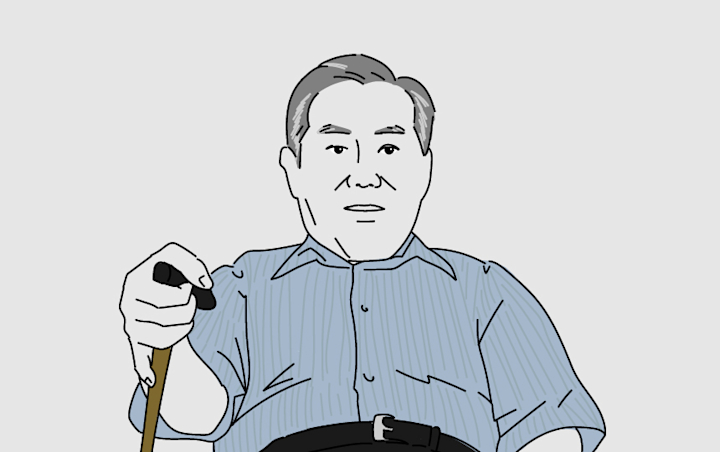左岸文化
2023-08-21發佈
2024-01-28更新
法律很爛?如何從自身改變?你聽過「法律動員」嗎?|話鹿讀冊

法律動員這個概念,在不同學者間有著不同的定義,他們對法律動員的概念範圍、手段或運用的場域各有不同的界定。在越來越多法律動員研究和文獻產出的同時,卻也呈現對於法律動員的不同理解。本文將娓娓道來。
快速跳轉目錄
什麼是法律動員?
法律動員這個概念,在不同學者間有著不同的定義,他們對法律動員的概念範圍、手段或運用的場域各有不同的界定。在越來越多法律動員研究和文獻產出的同時,卻也呈現對於法律動員的不同理解。
本章探查美國學界法律動員概念最早出現在布萊克(Donald Black)所著〈法律的動員〉(The Mobilization of Law),他將法律動員連結至耶林(Rudolph von Ihering)的《為法律爭鬥》(The Struggle for Law, 1879)以及龐德(Roscoe Pound)的《有果效的法律行動之限制》(The Limits of Effective Legal Action, 1969),定義法律動員為一個法律體系取得具體個案的過程,主要是要強調法律行動的「啟動」(set into motion)來自於公民,而非國家。
因此,布萊克使用動員一詞,比較接近中文「啟動」、「開啟」的意思,而非一般社會科學中意指集體行動的動員。其後蘭伯特(Richard Lempert)將法律動員定義為「法規範被引用來規制行為的程序」,他認為法律動員指涉兩個面向,一個是民間既有的糾紛開始與法律體系有所接觸,另一方面是引用法��律規範並期望政府機關有所作為。
本文認為,不論是布萊克或蘭伯特,他們所指涉的法律動員都是指私人間的糾紛進入法律體制進行解決的過程,因此他們所稱的legal mobilization更接近「法的啟動」的意涵,也就是在法體制內啟動法律程序的過程。然而,法律動員最廣為引用的定義為澤曼斯(Frances Zemans)一九八三年的〈法律動員:在政治體系中被忽略的法律角色〉這篇文章,她指出「當欲望和期望被轉化為以一項個人權利主張的要求時,法律就被動員了」。
這段日後廣為法律動員學者所引述的定義,置入了「權利主張」的要素,企圖透過這樣的定義,將法律動員的範疇擴張至法律程序開啟以前的程序,甚至包括在言語上訴諸法律的行動。
澤曼斯全文強調法律/司法系統作為政府權力之一環,不應忽略法律/司法系統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在這篇文章企圖指出,法律程序的啟動來自於個別公民,透過自主啟動法的程序,公民也參與了司法作為政府一部分的民主程序。
她認為,光是人民在個人行動中主張法律,就已經讓人民真正參與在政府架構之中,不須透過專業中介者或代表,直接成為法律的執行者。這篇對法律動員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將人民個人的「法的啟動」視為積極的公共參與行動,並可能進而形塑社會的改變,這使得法律動員跨越出了私人糾紛領域,進入了公共政治領域。
澤曼斯之後有更多的學者將法律動員研究的重心放在社會的集體行動,他們觀察不同的社會運動或社會改革如何將法律訴訟當作社會運動的策略或資源,以及分析法律權利在社會運動中的構成性角色,如何作為一種資源或限制、如何成為賦權或剝奪權力的來源,以及如何轉化和重新構成權力和社會關係。
自此,其後的法律動員研究同時擴及了個人私人間的糾紛解決過程、也包括團體或個人為了進行社會改革所進行的訴訟策略,尚格德(Stuart A. Scheingold)在其名著《權利的政治》二○○四年新版前言即將法律動員的研究分成兩種,一種為「個人的法律動員」,意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權利意識,另一種為「集體的法律動員」,意指權利被當作一種平等待遇爭取的資源。
新近的文獻也承襲這樣的看法,將法律動員同時包含個人的行動和集體的行動,例如范哈拉(Lisa Vanhala)即定義法律動員是「任何個人或是集體行動者引用法律規範、法律論述或符號以影響政策或行為的程序」。
對法律動員研究有著推廣熱情的麥肯(Michael McCann)則採取了廣泛的定義。首先,他有意地排除將法律動員僅限於訴訟或正式的國家體制管道,他認為來自法律動員研究的傳統是有意地將人民所啟動的各種法律或權利行動納入研究,並認為將研究重點從國家行動者移至在日常生活中掙扎的人民正是法律動員研究的標章,因此麥肯強調法律動員研究是以糾紛為核心(disputes oriented),而非以訴訟為核心。
其次,他強調法律具有多元詮釋的可能,法律傳統也僅構成我們對於事務或行動的複雜且交互作用的理解之其中一部分,而正是法意識這種多元且受情境影響(contingent)的特性,使得為法律動員所使用的法律本身呈現動態,而難以捉摸。最後,麥肯對於因果推論的研究方法和重要性採取比較質疑的態度,比起釐清到底採取訴訟策略是否真的帶來真正的社會改變的因果關係,麥肯嘗試建立的法律動員研究特別強調詮釋性(interpretive)方法以及探求構成性(constitutive)的因素,而非實證上的因果關係。
法律動員真的帶來進步嗎?
法律動員文獻大致分為兩種不同的取徑,如前所述,一種著重在個人所採取的法律動員行動,屬於個人間的微觀研究,另一種著重團體為主的法律動員行動,著重在鉅觀的社會改革和團體抗爭等。由於微觀的法律動員研究與本書的法意識研究有很大的重疊性,本章即不贅述。
社會團體爭取社會改革的鉅觀法律動員研究,多為政治學者所青睞。與微觀法律動員研究比較起來,鉅觀法律動員研究更加聚焦在訴訟(而非避免訴訟),因為社會改革訴訟幾乎都會上法院。
其次,鉅觀法律動員研究在美國幾乎集中在州或聯邦上訴和最高法院,而非第一級的事實審法院。在這一支的法律動員研究中,學者不見得會標示自己為法律動員研究,而常會使用「法與社會運動」這樣的概念,將法與社會運動兩者之間諸如「法律在社會運動扮演何種角色?」、「法律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如何影響對法律的理解?」,以及「法律動員真的帶來進步嗎?」這樣的理論提問作為研究的核心問題。
最早開始提出「法律動員真的帶來進步嗎?」的是一九七四年尚格德所著的《權利的政治》一書。他指出,儘管這些採取訴訟取得勝利的法院判決,但從實證觀察來看並不見得必然帶來社會改變。
也就是說,美國主流社會當時因為各種權利訴訟的勝利,一度以為權利訴訟是促成社會進步萬靈丹的這種信念,其實是一種「權利的迷思」。
然而,尚格德仍認為權利訴訟不失為一種政治動員的工具,他仍舊看到法律語言對於社會實踐的影響,以及政治動員中法律對於抗爭意義的形塑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但能夠活化沉睡的公民,也有助於將團體組織�為有效率的政治單位。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對於訴訟是否帶來社會改變的質疑日漸增加,羅森堡(Gerald Rosenberg)就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失落的期望》(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一書中,以民權運動、墮胎權運動和其他運動作為觀察的對象,舉出龐大的實證資料證明,前述之判決都不是真正造成社會改革的里程碑。
他認為這些運動將資源投注於訴訟當中,反而減少實質上對於社會改革倡議或其他作為的資源,其次,社會的改變是來自於社會運動由下向上的扎根與長期耕耘,而非單次的判決。本書對於法律動員的嚴厲批判,引發了大量的爭論。
最受注目的一個後續對話研究,咸認是麥肯的代表著作《工作權利》(Rights at Work: Pay Equity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Legal Mobilization),他承認,光是啟動法律訴訟本身,並不會帶來社會改變,但是他也認為訴訟代表著各種意義,應該以過程來論斷,而非以結果計成敗,法律的社會影響不應該只發生在體制層次。
在訴訟的過程中,不論是贏是輸,都有助於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及對於個人的動員,這些判決在潛在的訴訟行動者眼裡傳達了某些意義,進而影響了個人行動者的決定。這部重要的經驗性研究,不但重視法意識、個人行動,也討論了法律在各個動員階段中不同的意義,啟發了後續雨後春筍的經驗性研究,在法律動員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正是這樣的詮釋性研究,將重點放在法律建構社會意義的力量,轉移了法律在社會改變是否具效用性的核心爭議,學者不再專注於訴訟策略的工具價值,而聚焦在更複雜且受情境影響的「法律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問題。這樣的詮釋性轉向因而產生了許多精彩而細緻的研究。研究者發現法律讓行動者提�高了期望、產生義憤和希望、引起權利意識,並且有助於正當化社會運動的價值和目標。
在麥肯作品中,以及許多後續法律動員研究者所觀察到的法律行動者,對法律有著超越訴訟行動的理解,法可能被看作知識或是溝通工具,在特定的文化系統當中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可作為社會主體間建構意義的力量,法律因而成為一種具有可塑性的、多重意涵的資源,同時是社會抗爭行為中的規範性原則以及策略資源。
以美國婚姻平權運動為例,有許多文獻針對美國婚權運動大量採取訴訟策略進行評價,羅森堡也在二○○八年新版的《失落的期望》中增加了對於婚姻平權法律動員的分析,同樣對於此種訴訟策略感到悲觀。
有學者甚至認為訴訟策略對同婚進展其實弊多於利,例如一九九六年夏威夷最高法院的合法化判決反而帶來州的修憲,限制婚姻為異性婚;還有學者認為採取訴訟策略造成自由派的選舉失利,讓婚權立法更加困難。
然而,也有許多研究者透過更細緻的分析觀察婚權運動,發現在受到反挫(backlash)的過程中,反而為同志權益帶來法律和文化上的轉變,或是發現勝訴結果會對其他州帶來激勵作用,進而採取訴訟策略,或是使得支持者更願意投入地方草根工作。
埃斯克里奇(William Eskridge)則提出證據指出,在訴訟上成功卻於政治上遭到反挫的例子,可能是訴訟提出的時機過早,或是在草根組織還沒有階段性進展時就提出訴訟,如果草根組織有一定的基礎,團體在仔細評估之後提出訴訟,如此得到的勝訴就可帶來運動所欲的成果。
官曉薇二○一九年的〈婚姻平權與法律動員──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前之立法與訴訟行動〉一文,即是以台灣婚姻平權法律動員為例,與前述的理論進行對話,發��現台灣的婚權訴訟並不是在完全沒有草根組織或立法策略的情況下所提出,在提出訴訟的過程中,婚權團體其實了解不能完全依靠法律動員,因為他們預測在台灣的憲法訴訟結果仍須回歸立法,最終還是得打一場立法戰,而正向的大法官解釋結果則可作為立法遊說時的政治槓桿。
上述研究亦可看出此種晚近較細緻分析法律動員過程的研究很具有啟發性,不過法律動員研究中這個核心的議題──法律究竟帶來社會改革還是反挫 ──恐怕還是要觀察不同社運的脈絡和過程來進行分析,很難一概而論。
【本文作者】
官曉薇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法律與社會運動、法律動員、國際人權規範之法社會學、性別與法律。
【本文出處】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法律有關係:法律是什麼?怎麼變?如何影響我們生活?》
第十八單元〈法律動員:法律真的能帶來改變嗎?〉部分
* 本專欄「話鹿讀冊」,分享法白關注的書籍,希望你也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