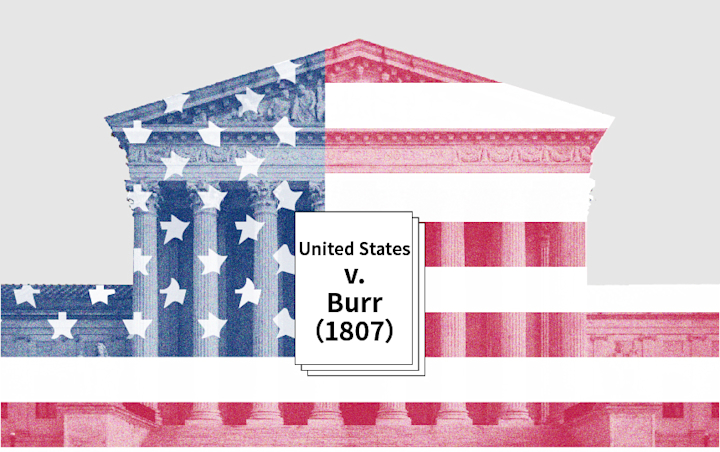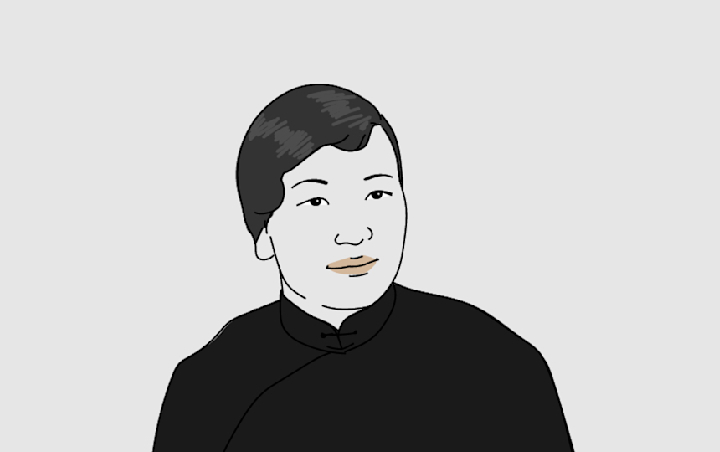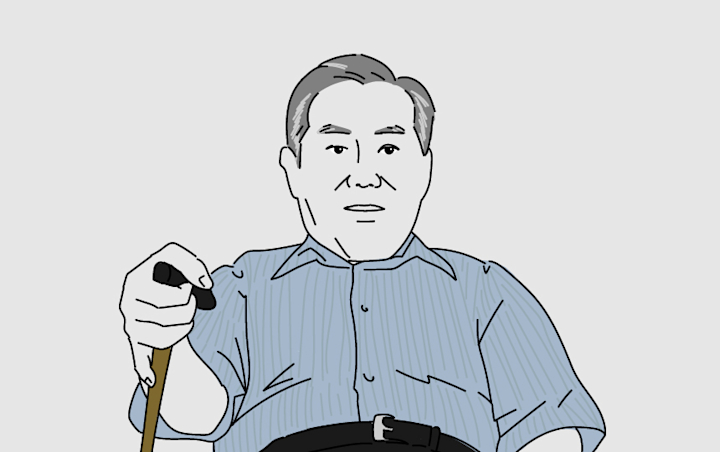李柏翰
2016-08-27發佈
2023-03-05更新
在嚴懲與減害之間:淺談國際藥物法|李柏翰

這場「只許勝,不許敗」的仗,是否應由警察主導,代替月亮來懲罰用藥者?其他「減害」措施應否且何時介入?這麼多年的風聲鶴唳所造成黑市、劣品,以及用藥社群的人心惶惶、健康疑慮等問題,除了丟到各種機構(不論監獄或醫院)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作法?最後,如何能減緩整體社會的各種壓力呢?
在嚴懲與減害之間:淺談國際藥物法|李柏翰
在台灣,毒品一直是個極具爭議的話題,總統今年出席警察節慶祝大會時,指示「反毒戰爭」只准勝不許敗。近來有快卸任的立委提出「施用毒品罪醫療前置化」新方案,調整管理用藥者的規範與手段,卻遭到名嘴奚落與痛批。與此同時,菲律賓新總統Rodrigo Duterte上任以來,也因爆衝反毒的關係,引發許多爭議,雖然他明擺著「不在乎人權」,但究竟國際法是怎麼說的呢?
感覺每個政府都視毒品為洪水猛獸,很多人就算沒有親自接觸過「藥」或用藥者,仍不自覺很反感(政府文宣太成功),時有所聞的大概有社會魯蛇論、全家遭殃論、拒受干擾論。在這麼多元且複雜的社會關係中,設定「怪物」是首要策略,各國都有自己的方法,不過愛出鋒頭的國際法在這件事上也不缺席,甚至扮演了蠻重要的角色,不同情境中有不同boss 要打,打法也不同,這就是這篇文章想介紹的。
實際上,把所有drug皆視為有毒物質,即「帶『毒』的物『品』」這個概念只存在於中文的語境中。聯合國官方翻譯也為中國代表(不論1971年前後之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而多翻為毒品。這裡不談「轉譯」的政治學,不過單就英文而言,drug是指任何不是「食品」而對人體會產生生理反應的物質。各種受管制的「藥品�」(medicine)也是drug的一部分,主要用途與治療或預防疾病有關。
對個人的精神與肉體來說,drug真正衍伸的問題是「成癮」(addiction)和「濫用」(abuse)。由於每個人的精神狀況、體質、人際關係、用藥情境都不一樣,因此「藥+人=毒?!」是很難一言以蔽之的(如食藥署管檢字第0970010804號之說明),大抵只能從統計數據或生物醫學來說個大概(也總有例外)。這也是為什麼「藥」會充滿爭議,在於它兼具天使與惡魔的性格,「用得好讓你上天堂,沒用好送你下地獄」。
有鑑於網路上已有許多討論,從公衛、歷史、犯罪學角度看門道的,到靠直覺、風向、想像力看熱鬧的都有。除了各種釣魚手法或驚悚文宣以實現「把人變成罪犯」(criminalised)的政策目的外,現在也有其他許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把人變成病患」(medicalised),或從一個減害(harm reduction)的角度,「把人變成需要幫助的人」。
為了不想直接給予價值判斷,以下將把「毒」都改成中性的「藥」、「物質」或藥物名稱。這個作法是希望能讓讀者用不同的語言吸收下列的資訊,或許能進一步重新評估對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東西的看法。
多邊體系的建立
當年在建立全球多邊體系時,力主全面打藥的美國一直想將國際法「美國化」的野心終究沒有實現,主要是因為「(原料)生產國」、「(藥物)製造/加工國」、「(藥物)消費國」三個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相互協調下,為促進國際合作的意願,再加上麻醉品與精神藥物的確具有相當程度的醫學實用性,最終採取「控制」而非禁絕的管理模式。
因此在國際藥物法(international drug law)的構想中,針對非法產銷/非醫療使用之擴散才是關鍵,如何妥善管�理生產、加工、消費成為整個制度的核心。
二戰前,各種管制條款原本散落在不同條約、機制中,但在國際聯盟垮台後宣告失敗。聯合國成立時,「整合管理」的構想成為倡議主軸,好巧不巧後來又碰上冷戰,偏偏主要生產國大多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如蘇聯、南斯拉夫),加工製造者則集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如美國、法國),消費群眾則到處都有,因此彼此產生許多分歧,甚至一度熱炒的國際檢查制度,也因各國主權考量而胎死腹中。
例如,原本1963年生效的《限制和管控罌粟種植、鴉片生產、國際和批發貿易及使用議定書》(Protocol for Limiting and Regul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oppy Plant, the 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Wholesale Trade in, and use of Opium)對於鴉片生產、國家專賣、許可證制度都有嚴格規定,然而保加利亞、蘇聯和南斯拉夫等主要生產國都未參加,致使該協議形同虛設。
後來,更受國際社會歡迎的《麻醉品單一公約》(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生效後,依第44(1)條之規定,取而代之。這項公約被國際社會譽為「全球藥物管制體系的法律基礎」。後來聯合國再通過《精神物質公約》(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s),增列了原本沒有規範到的「其他精神物質」。
然而,更重要的是,該公約亦把藥物濫用相應的康復、治療、照護、教育等社會服務與懲戒措施並列,甚至在條文安排上,優先於刑罰的條款。這個改變也反映在1972年通過的《修正1961年公約議定書》(Protocol amending the 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上。

後來,1988年聯合國再通過了一項《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物質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與前兩個公約共同建立起全球藥物管制的多邊體系。三項公約的爭端解決辦法原則上都一樣。爭端發生時,各國應先相互諮商,再透過談判、調查、調停、和解、仲裁、區域性辦法等和平手段處理。如解決不了,得提起國際法院裁判。
這個系統主要是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SOC)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專責機關。前者成了國際麻醉藥管制委員會(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的上司,並另設麻醉藥品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CND),兩個機關分別具有準司法及準立法之功能。
至於為人熟悉的聯合國藥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則是一個兼具警察調查、政策宣導、公眾教育性質的行政機構,成立於1997年,合併了原本的聯合國藥物管制規劃署(UN 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Program)與犯罪預防與刑事正義委員會(Commis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兩個機構。
藥物管制的彈性
由下表可見,「管制」是採列舉式立法(即依藥物性質、化學式及相應處遇方式分類)。操作上,是彈性調整的空間,也是爭議疑慮所在。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舉例而言。因應近年來逐漸在中國國內流行的K他命(氯胺酮化合物),中國政府於2015年曾通知主管現行公約體系的CND,希望能將K他命改列入1971年公約附表一(即最嚴格之控管,包括醫學上之使用)。然而,依WHO統計,全世界有百萬人口需仰賴氯胺酮來完成外科手術,且許多獸醫麻醉亦經常採用相關製品,因此中國修改了其提案,建議改成附表四(即最不嚴格之項目),但因反對聲浪大而尚未成案。
在藥物管理上,WHO認為在打擊各種藥物的同時,不可以忽略它們在許多國家作為基礎藥物(essential medicines)的意義,否則將導致健康不平等的情況。
從這個案例可以發現「公共健康」的視角逐漸取代「打擊犯罪」的模式。事實上,不論是1961年公約、1972年修正議訂書或1988年公約的官方評釋(Commentary)皆強調了藥物控管的政策目的在於「全人類的健康與福祉」,認為一味打擊犯罪是不夠的,國際社會開始調整腳步,推行能夠產生正面功效的關懷康復制度。
較為成功的作法,像是1990年代許多西歐國家採取的「海洛因輔助治療」(Heroin-assisted treatment),是一種從「需求面」著手的角度,由政府提供美沙酮或其他替代物質,以及安全、衛生的注射環境,藉此逐漸降低需求者對海洛因的依賴度。這個作法最大優點在於,黑市相對失去誘因與競爭力,且這種多重照護方式也較能避免共用針頭的感染問題。
包括WHO和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在內等許多國際機構都曾表示,無論是公衛或人權立場,深化「藥物」汙名與用藥者標籤的措施,除了直接或間接造成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外,幾乎沒有幫助,而弱勢群體中的用藥問題往往涉及結構性的因素,卻容易被刑法偏重的「個人行為」給忽略了。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目前全世界有上百萬人因輕微或非暴力的藥物使用被關進監牢。」反例則像是葡萄牙2001年將用藥全面「除罪化」(decriminalised)的創舉。除罪化不等於「合法化」(legalised),故持有、使用藥�物雖沒有刑責,但仍有行政罰上的法律效果,而販賣、走私則仍屬刑事管轄,十幾年下來成果斐然。除罪化當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不過相應的社會福利、公共衛生政策也是關鍵。

近幾年,UNODC不斷強調「刑罰化」個人藥物之使用或持有「並非」公約義務,敦促國家不要以此作為藉口。考量到聯合國法律規範體系的三大支柱「安全、發展、人權」,國家在處理藥物問題時,應考慮到個人「健康權」的面向,以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於2000年通過的第14號一般意見書及聯合國健康權特別報告員年度報告中的建議。
此外,UNODC也經常援引1984年由ECOSOC通過的《錫拉庫薩原則》(Siracusa Principles on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要求各國於立法或執法時(不論採取強硬或柔軟的態度),各項政策都應考慮到《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中相關法律義務。
傾聽優先於打擊
今年,UNODC提出「傾聽優先」作為「國際禁止藥物濫用和非法販運日」的主題。許多藥物政策改革的倡議組織,比如國際減害組織(Harm Reduction International)、國際藥物使用者網路(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People who Use Drugs)、國際藥物政策聯合會(International Drug Policy Consortium),也將每年7月21日訂為「藥物使用者紀念日」,希望促進人們對那些「人間失格」的他者多點關懷、少點歧視。
儘管用藥、持藥與販藥,在法律上的評價不盡相同(行為不同,「想像中」的傷害也不一樣),國際法和我國國內法也將兩者分別評價,但理性社會原則上仍是不太允許個人迷失的,就算這是個普遍不滿的世代。受控、有相當社會支持或健康資本的人,或許還能在緜密的人際關係中找到放空的小確幸,但失控的多半會直接被判定為「有問題」。
「成癮」是現代社會建構的概念,它雖然稍微緩和了近乎偏執的反藥戰爭,卻也再度確認了每個人必須保持「清醒」才有競爭力、才是合格公民的進步主義。在舊觀念、新證據匯集的地方(比如台灣),則都還處在用藥「是罪,也是病」雙重打壓的尷尬狀態,許多「用藥去死剛好」的言論,其實反而讓身邊苦於物質濫用的人「不敢出櫃」。
隨著不斷增修的藥物清單,某些物質在公眾意識中早已形成「不正當/不健康」的象徵性意義,也讓用藥者社群因此被噤聲。比如,今年七月下旬的第21屆國際愛滋會議(International HIV/AIDS Conference)約有兩萬多人湧進南非會場,唯獨不見「用藥者社群」,許多倡議團體表示遺憾,也足以證明在攸關自身權益的場域中他們亦難有一席之地。
結語
最後,談一下容易搞混的分級制度。國內與國際政策經常有不同的考量,比如在我國列為三級毒品的K他命,並非國際公約的管制藥物,主要是因為國際社會須考慮各國基礎藥物的需求,但國內只需要考慮藥物的「健康危害」。又如另一種二級毒品的MDMA(搖頭丸主要成份),在《1971年公約》裡則列在最嚴格的附表一裡,因為「毫無醫學上之功效」。
從管制藥物的角度來說,「許可制度」是最普遍的作法,例如衛福部食藥署回覆台北地院的管字第 1039900715 號函中指出:「醫藥上使用…經衛生福利部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輸入及輸出」,因此未經核准而輸入的,則屬於禁藥(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若是擅自製造的,則屬偽藥(藥事法第20條第1款)。

回到最一開始提到的菲國反藥戰,人權組織批評的「就地正法」或「無證羈押」等作法的正當性,都甚至還牽扯不到除罪與否,就已經引來許多恐藥者的擁護。然而,對於那些受牽連的其他人,在這個不缺女巫的時代,除了急著替他們把親友、鄰居、路人妖魔化外,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暴走的正義感,有沒有可能也是出於一種道德認同焦慮呢?
從這件事的發展或許能讓我們借鏡,思考這場「只許勝,不許敗」的仗,是否應由警察主導,代替月亮來懲罰用藥者?其他「減害」措施應否且何時介入?這麼多年的風聲鶴唳所造成黑市、劣品,以及用藥社群的人心惶惶、健康疑慮等問題,除了丟到各種機構(不論監獄或醫院)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作法?最後,如何能減緩整體社會的各種壓力呢?
參考資料
張勇安,《多邊體系的重建與��單邊利益的訴求:以美國批准聯合國「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單一公約」為中心(1948-1967)》,歐美研究,第36卷第2期(2006),頁315-357
Alex Stevens, ‘Portuguese drug policy shows that decriminalisation can work, but only alongside improvements in health and social policies’, European Politics and Policy, 2012-12-10
Glenn Greenwald, ‘Drug Decriminalization in Portugal: Lessons for Creating Fair and Successful Drug Policies’ (Cato Institute, 2009)
Jason Nickerson, ‘The Global Movement to Preserve Access to Ketamine and Raise Awareness of the Global Disparity in Access to Controlled Medicines‘, IDHDP News, 2016-07-02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 ‘Public health dimension of the world drug problem includ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World Drug Problem‘, EB138/11, 2016-01-15
Report of a GDPO/ICHRDP/TNI/WOLA Expert Seminar, ‘International Law and Drug Policy Reform’, 2014-10-17/18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on the 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 1961’ (UN, 1973)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on the Protocol Amending the 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 1961’ (UN, 1976)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1988’ (UN, 1998)
UNODC, ‘Decriminalisation of Drug Use and Possession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Briefing paper, 2011-10-19
William McAllister, ‘Drug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封面圖片:calvinfleming via Visual hunt / CC BY-NC-SA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