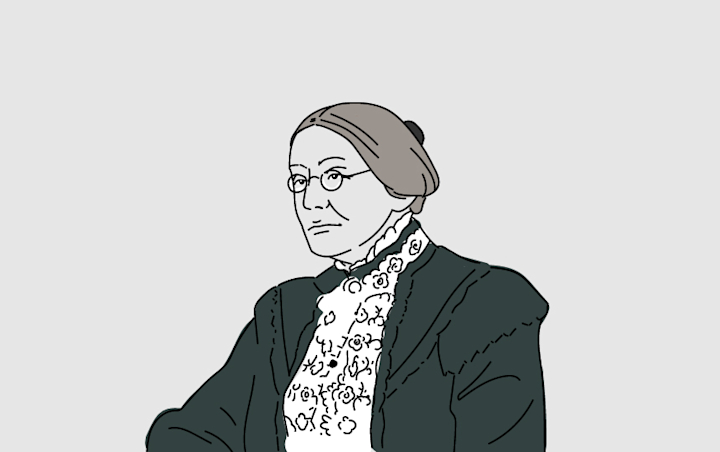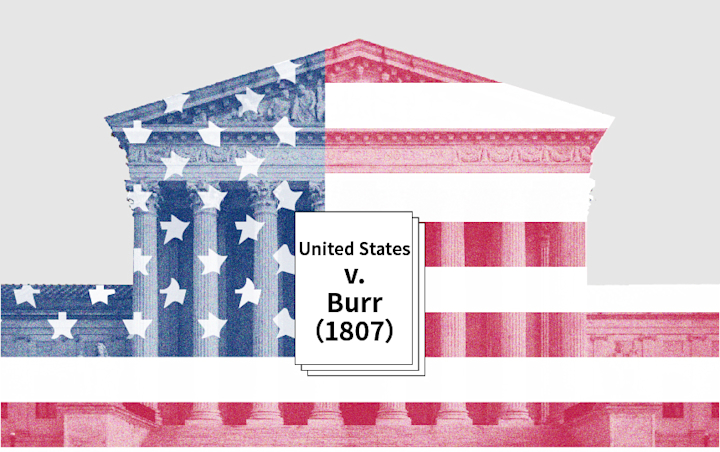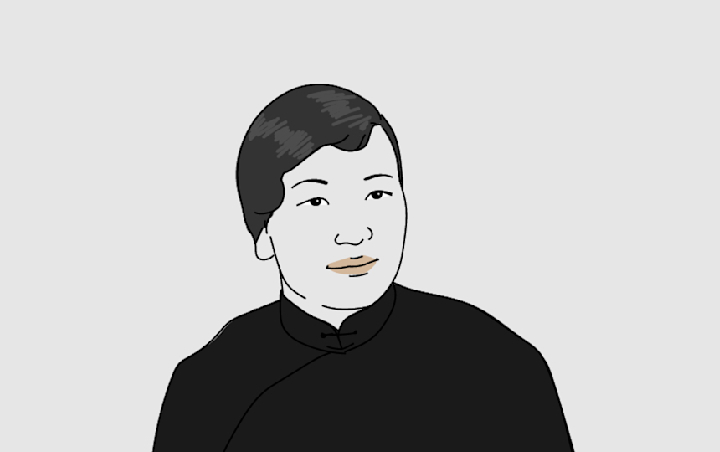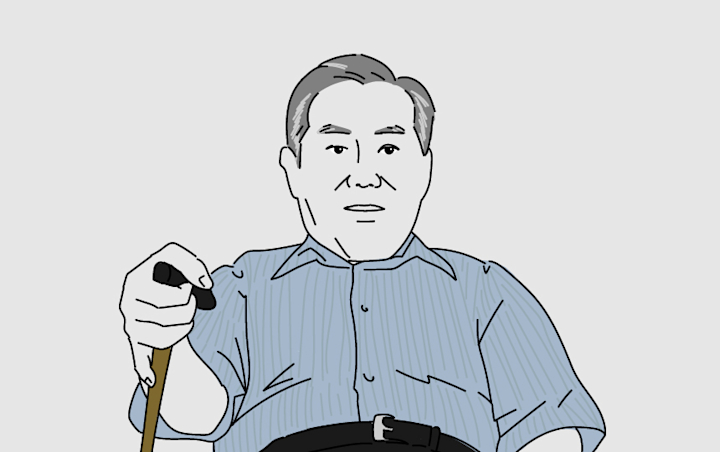臺灣商務印書館
2022-09-25發佈
2023-03-06更新
納粹如何興起?怎麼會讓民主上了絞刑台?|話鹿讀冊

本文摘自商務印書館《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 …
納粹如何興起?怎麼會讓民主上了絞刑台?|話鹿讀冊
本文摘自商務印書館《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
第七章〈馬克斯.韋伯論領袖: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這一章的主角也是一門講座。這場講座剛好比康斯坦在一八一九年巴黎發表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晚了整整一百年。這是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慕尼黑為一群學生所做的演講。這是與康斯坦的演講截然不同的場合,也是一場非常不同的講座。有些人宣稱,這是現代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演講。
康斯坦演講時,他與演講中分析的核心事件已經有了些歷史距離。而這樣的距離,讓他得以用後設的眼光回顧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韋伯沒有辦法如此。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慕尼黑是當時政治風暴的核心,而韋伯親赴現場,為這場風暴辯護。
慕尼黑是巴伐利亞的首府,當時巴伐利亞正在經歷一場受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啟發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月時,這場巴伐利亞革命已經持續了幾個月,而它將很快地被一場反革命扼殺。在那之後,是大量的流血鎮壓。巴伐利亞所屬的國家──德國──在當時彷彿正處於內戰邊緣。在一九一九年年初,這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運作的機能,德國的��政權在兩個月之前宣布投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劃下終點的同時便已瓦解。
當時的德國匯集了霍布斯所說的政治災難的三重奏:軍事災情、革命與內戰的萌芽。這也是政治末日啟示的三騎士。
我們和康斯坦一樣,有著後設視角所帶來的優勢,而這可能使我們難以重新掌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與開放性。對我們來說,難以掌握當時的情境的難處在於我們有太多的後見之明。我們知道德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德國並沒有爆發內戰;德國確實建立了一部有效的憲法、成立了一個得以實質運作的國家──威瑪共和,儘管這個國家很快就失敗,並且被另一種國家(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國家)所取代;而我們也知道,那個繼之而起的國家都做了些什麼。
對我們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結局是一個更長的故事,我們也習於將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事件置入這個更長的故事裡。但韋伯不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他也沒能活著看到那些事件的到來,這是因為在當時,除了那政治災難的三重奏之外,還有另一種力量在干涉著政治與社會,而這股力量更接近《啟示錄》中所說的騎士:流行病。西班牙流感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冬天肆虐,在爆發的十八個月內奪走數千萬條人命,包含韋伯。
我們可以試著用一種方式來重現這種戰後的不確定感(也是這種不確定感催生了韋伯的講座),而這會讓我們必須講述一個很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故事。我們傾向於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耗時四年史詩一般的痛苦掙扎,造成了慘重的損傷、總會陷入僵局的戰事、成為象徵的壕��溝戰,最終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只能付出巨大的人力成本來確保勝機,而這樣的慘勝很快就被隨之而來、帶有懲罰性質的和平所浪擲。
但對於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來說,這不僅是一場歷時四年的煎熬,也不僅是一場僵局。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為戲劇化也難以預測,更非毫無意義。對經歷戰事的人們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像坐上了有著漫漫長軌的雲霄飛車。
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兩場戰爭,儘管我們習慣把它們混為一談。第一次戰爭從一九一四年八月持續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這更像是一場歐洲的內戰。內戰的一方是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另一方則是中歐和東歐大國: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和保加利亞。這場內戰最終蔓延到這些國家基於帝國主義在全球各地所占有的領土,但總歸來說本質上還是一場歐洲自相殘殺的戰爭。對許多被捲進這場戰爭的參與者來說,這場戰爭真的沒有太多意義,參戰的人員以過度的愛國情操和軍事化的國族主義激情來取代戰爭本身欠缺軍事邏輯的事實。這場戰爭變成一場無解僵局,且在經歷了兩年半的痛苦掙扎之後,戰爭看來毫無出路。
然後在一九一七年春天,爆發了兩件事,而這兩件事徹底改變了戰爭的本質,並將這場歐洲內戰演變成一場真正的全球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件事情是俄羅斯革命。這不是同年稍晚爆發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而是二月份的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它試圖以類似憲政與自由民主的體制來取代沙皇和帝制政權。
對許多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來說,第一次俄羅斯革命的影響在於它讓人們開始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是人們��第一次可以宣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為民主而戰的戰爭。這場戰爭揭開序幕時,當時歐洲兩個主要的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與尚未成為民主國家的俄羅斯結盟,但正如托克維爾曾預期的,在未來會發生的史詩般的重大戰爭,是民主對抗俄羅斯的戰爭與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相比,當時俄羅斯政權更像是中世紀的神權政治。
但是當那個神權的、神秘的、極其無能的政權在一九一七年悲慘的冬天瓦解,並被民主政體取代時,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終於可以共同宣稱,他們不僅在軍事上是同一陣線,在政治上也是,而這樣的宣稱,吸引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注意──美國。
一九一七年春天發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美國參戰了。美國之所以參戰,不全然是因為俄羅斯現在是新生的、需要被捍衛的民主國家,但這仍然是它參戰的部分原因。隨著美國參戰,這種新的權力部署讓原本呈現僵局的軍事平衡開始朝著顛覆德國及其盟友的一方傾斜。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團結了起來,以擊垮他們眼中威脅歐洲核心民主國家的敵人。
但如果在一九一七年年初,事態看來對德國極為不利,那麼到了一九一七年年底,事態又開始變得對德國極為有利。因為到了年底,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已經被第二次革命所取代。試圖在俄羅斯建立自由民主政權的嘗試最終只能宣告失敗,而那個政權在死亡前並沒有能留下什麼遺緒。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這個政權來說太過宏大,而試圖以民主為名來進行這場戰爭,最終只是拖垮了俄羅斯的民主。當布爾什維克上台時,他們的第一個舉動幾乎就是宣布他們想不計條件地退出戰爭,因為這��不是他們的戰爭,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持續參戰的打算,他們有其他的戰事要處理。列寧投降了,這是一次全面投降,而這或多或少地給了德國人想要的一切。德國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受到威脅,因為同時在東方和西方兩條戰線作戰。而現在,德國可以將注意力轉向西方,雖然還是必須留心東線,因為擔心方興未艾的俄羅斯內戰會蔓延到德國新近取得的領土,也意味著德國必須投入軍隊來恢復東部領地的秩序,但這已經足以讓極多的人力西移,投入西線為最終決戰做準備:與西方民主一決生死。
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應該要發生,卻沒能順利發生的事情。美國的參戰並沒能拯救英國與法國,因為美國沒有及時加入戰場、沒有派出足夠的人手、也沒有對戰爭帶來太多變化。因此,到了一九一八年春季,德國看來正一步步地邁向戰爭的勝利。到了同年初夏,倫敦、巴黎甚至華盛頓都開始感到恐慌。德國人向西線推進,彷彿就快要占領巴黎,也突破了壕溝戰的僵局,眼看著就要拿下勝利。一場無意義的消耗戰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體驗:這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以及一場被命運劇烈波動影響的戰爭,接著,突然之間,事態果斷地朝著對德國有利的方向發展。
這就是站在歷史的遠方回顧時難以記得的事。在一九一八年前半,德國幾乎就要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在幾個月,甚至幾週之後,形勢突然逆轉了。不久之後德國的政權徹底崩潰。德國的軍隊有一部分也崩潰了,但不曾全然崩潰過,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在軍事上並未嘗過任何決定性的潰敗。
這次的潰敗是政治上的潰敗,因為德國的政治領袖投降了;這同時也是社會��的潰敗:飽受病苦、挨餓,瀕臨破產的德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德國再也無法承受打這場戰爭所需的成本。當支應戰爭所必須的一切努力開始失去效力,戰爭也將很快地潰敗。到了一九一八年年底,德國在第一次全面戰爭中徹底戰敗。德國皇帝遜位、政權也被載入史書,德國必須要建立一種新國家。這是韋伯演講的更宏觀的脈絡。當時存在著騷亂,也存在著苦難,但與此同時,也有著深刻的震撼感。
但新的國家還沒有建立。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德國各地,尤其是巴伐利亞,有些人試圖建立無產階級主政的共和國;而在柏林,人們正努力為一種新的、現代的憲政秩序奠定基礎──這將成為後來的威瑪共和國的起源。韋伯造訪慕尼黑,部分原因是他想要當面告訴他的聽眾,他認為危在旦夕的事情。
他直接面對面講課的對象,是參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學生,但他同時也間接地向柏林的政治家們發言。他認為他不能告訴這些人應該如何以落實政治。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韋伯演講的一個核心主旨是,在政治上,你永遠無法告訴那些擁有做出重大政治決定權力的人,他們應該怎麼去做出決定。因為該怎麼做決定,終究是個人選擇與個人責任的問題。但他確實認為,在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風險和政治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任何負責任的政治家在做出抉擇時,都必須考慮不同的因素,而他想把這些因素們說出來。
韋伯這場講座的德文原標題是:「Politik als Beruf」。這很難翻成英文。「Beruf」這個詞不只有一個意涵,它的意思既是「職業」(profession)也是「志業」(vocation),因為「Beruf」既意味著一份工作(你以什麼為生、如何賺錢),也意味著��你的使命(賦予你的生命意義,同時讓你得以營生的事物)。
而正如韋伯在他的講座中明言的,政治在現代國家裡兩者兼具,它既是工作的潛在來源,也是意義的潛在來源。正因為韋伯賦予政治這樣的雙重性,使得這個講座如此具有現代的特質。但同時,這場講座也呼應著其他事物。韋伯的演講在最後幾乎變成了某種布道。他並沒有指引著人們應該做些什麼,而是要人們審視自身,反思他們被期望能做些什麼,以及這麼做又意味著什麼。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現代政治史中最重要的世俗布道。
德國在一九一九年年初的處境,可以說是霍布斯式政治最為原始的形式,因為有太多事物懸於一線,也因為事態存於隨時崩壞瓦解的高度危險之中。這是個在戰爭中被擊敗、被流感肆虐的國家,人民無以充飢、政治人物慌張無措、而革命人士正在高歌前行。在當時,有許多離開戰場的軍人並不認為自己戰敗了;更不幸的是,他們多數人認為他們被政治家背叛,因此許多軍人仍舊全副武裝。也因此,當時極有可能發生規模更廣的革命。德國似乎正處於政治災難的邊緣。
這是現代德國政治史上一個特殊的霍布斯式時刻,霍布斯絕對會意識到其中的風險。然而還有其他事物連結了韋伯與霍布斯。首先是韋伯在他早期的著作裡,提出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定義,而這可能仍舊是最著名也最為簡潔的定義。
這個定義同時也具有明顯的霍布斯色彩。韋伯嘗試著用幾個詞彙來總結國家的特質。他說國家(現代國家)是一種「成功宣稱它可以合法地壟斷強制力」的群集。這句話有時候被更直白地轉譯為「國家對暴力的合法壟斷��」。他用這五個詞彙來總結國家的特質:成功、宣稱、壟斷、合法、暴力。而在這五個詞裡,最容易脫穎而出的是壟斷與暴力。國家是壟斷暴力的實體,也是個製造並使用暴力的機器──這是利維坦可能存在的最為殘酷的版本,但真的讓韋伯的定義染上霍布斯的色彩並賦予他對國家的理解力量的,是壟斷與暴力以外的其他詞彙。
國家不只是宣稱它壟斷暴力,它的暴力必須是「合法」的。沒有事物得以宣稱它們實質上壟斷了暴力,因為暴力總是能夠以一種超乎各式宣稱的形式被展現。沒有國家可以廢除國家以外的暴力:家庭暴力、刑事暴力、結構性暴力都持續存在,但是在現代國家中,只有國家得以使用暴力、只有國家得以進行脅迫,也只有國家得以強迫人民去做國家想達成的事情,甚至如果有必要,國家會迫使人民在槍口下行事。
然而重要的一點是,這只是一種宣稱。任何國家都會宣稱能做到這一點,但只有正常運作的國家可以讓這樣的宣稱成功執行。這種對暴力的壟斷成功與否,取決於人民是否接受這種宣稱,而接受的人民同時也必須要承受可能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
主權的權力與人民因此是一種連鎖關係: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接受了國家的宣稱,而這之後人民臣屬於這種背後有暴力支持的權力之下;最終,這讓人民沒有辦法從合法性的角度上,對權力與暴力提出挑戰。因此,讓這個論述充滿霍布斯色彩的並不在於暴力被壟斷了,而是在於壟斷取決於人民承認了這種壟斷的合法性。當這個情況發生時,主權權力與人民被相互鎖在一起。
韋伯曾經給予民主一個更粗暴的定義。他說民主��只意味著我們選出了某個人來為我們做決定,而如果決定嚴重出錯了,「那就和他一起上絞刑架吧!」把君主送上絞刑架一點也不霍布斯,但這種我們選出某個人來為我們做決定,而且我們不必對這個決定有所付出(換言之我們允許有人以我們的名義行使那不被約束的權力),是非常霍布斯式的觀點。
另一個韋伯與霍布斯的連結在於,他們都是科學家。韋伯是一位社會科學家,而霍布斯則認為自己更像一名自然科學家,儘管在霍布斯的理解中,自然科學的範疇也包含研究社會。但真正聯繫兩人之處,在於他們都相信他們所信仰的科學揭示了既有的政治科學的極限;當然在霍布斯來說,是理性的極限。
如果我們回到霍布斯的論點,他基本上在說,如果你純然利用理性來思考政治,你會意識到你的理性論點終會有所侷限,因為政治決策終究未必要是理性的──而理性上來說,你必須要接受政治決策的結果,即便政治決策未必是理性的。或者我們換句話說,霍布斯從來不曾說過主權者必須是理性的,能夠清晰思考的主權者將比無法清晰思考的主權者做得更好,然而,對於霍布斯的論點來說,尤其重要也不可或缺的是主權者的決策,而決策本身卻未必需要是理性的。
韋伯對同樣的論點有一個不同的版本。他認為社會科學,包含社會學、政治科學、歷史學都可以教導我們許多關於政治如何運作、制度如何發展、哪些制度會比其他制度還要好的相關知識。但這些都無法教導我們,政治家們會做些什麼。更直白地說,韋伯並不認為社會科學會教導我們最好把政治交給社會科學家來治理;事實上,他的想法正好與此相反。他認為政治不是科��學家擅長的場域,如果你活在由科學家做出決策的國家,這表示你有麻煩了,因為科學家不是政治家。關於政治,你的社會科學所應該教導你的內容幾乎有點套套邏輯:政治事務最好還是交給政治家。
韋伯擔心的不僅是科學家而已。他認為有許多職業根本不適合參與政治,學術界便是其一。他認為政治不應該交給那些不太擅長做出決定、認為在有決定性的證據或證明前辯論應該無止盡地持續下去的人,而學者便不擅長在沒有確切證據、充滿不確定的情境中做出決定。在韋伯看來,適合參與政治的職業是律師與記者,因為他們習於隨著事態發展的過程做出抉擇。韋伯認為另外還有一組人也不適於從政,而我很快地就會談到他們。
於是乎,對韋伯來說,科學的思考政治所得到的結論,就是政治不應該交給科學家來治理。但韋伯和霍布斯之間還是存在著許多差異,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人相距近乎三個世紀。一九一九年的德國與十七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完全不同。
其中一個不同之處是,在一九一九年年初的德國,那場看似在醞釀之中卻未曾爆發的內戰並不是一場兩個派系之間的競逐關係,而且也沒有拋出非此即彼這種前現代政治的選擇。當時德國醞釀的內在衝突至少是三向的,因為一九一九年德國所擁有的其中一個選擇,就是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在當時的德國,有些人既不尋求推動革命性的變革,也不追求把這個新的世界帶回到數個月前他們所拋棄的那個舊體制裡。讓我們姑且把這兩方稱之為後現代政治的擁護者與前現代政治的擁護者。後現代的一方包含了布爾什維克、斯巴達克同盟(Spartacists)與其他社會主義夢想家;前現代的那組,則包括一些原初的法西斯主義者,以及希望德國皇帝復辟,甚或是希望得以重建一戰期間的德意志帝國且曾在當時為之戰鬥的人們。
因為在這些人的腦海裡,他們從來不曾在戰場上被真正擊敗過。換言之,在當時的德國有些人希望能讓時間倒流。但,除了上述兩種人,德國也有一些人希望能夠繼續堅持著新的秩序,希望能在德意志帝國瓦解的灰燼上重新建立新的德國,無論這麼做的結果是好是壞。讓我們稱這群人為現代政治的擁護者。韋伯就屬於這麼一群人,而這群人也將會創建威瑪共和。
與韋伯本人不同的是,這群現代政治的擁護者中,有許多人是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多數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且在理論上(如果不曾付諸實踐)相信共產主義革命的改革力量。但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後,其中一些政治家開始察覺,如果他們實際審視當前的形式,那麼德國所需要的將會是自由憲政國家。
這讓他們竭盡所能地想創建一個憲政德國。韋伯的演講中,部分是在向這些政治家們喊話,告訴他們要保持冷靜、放手去做他們需要做的事情,也要牢記在政治的場域裡,沒有什麼決定是簡單、純粹或道德的。韋伯選邊站了,而這與霍布斯截然不同。韋伯選擇站到了現代國家的陣營,這意味著他比霍布斯更靠近我們今天稱之為「建國」(state-building)的實質事務。
作者簡介 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
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2018年被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2021年進一步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院士,英國知名政治評論家。長年�研究現代政治思想、國家和政治理論,關注民主的脆弱與延續,著有《民主會怎麼結束: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等書。他定期為《倫敦書評》撰寫政治相關文章,且每週定期主持廣受讚譽的Podcast節目《談談政治》(Talking Politics)。
譯者簡介 陳禹仲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中心助研究員。喜歡閱讀、旅行與曼徹斯特聯隊。目前的研究主題是疫情政治中的政治情緒。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