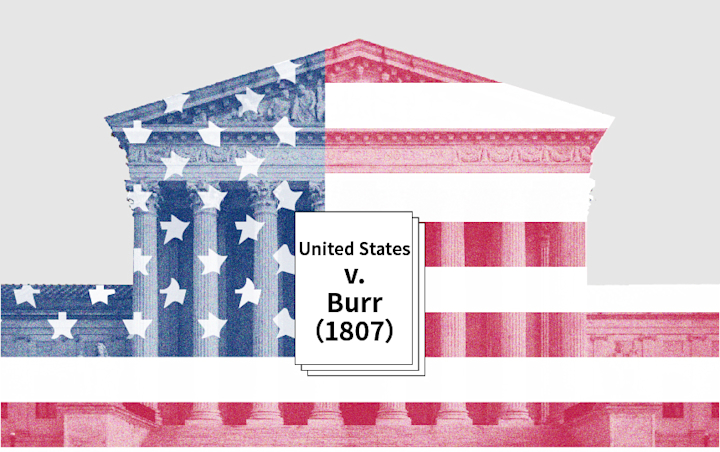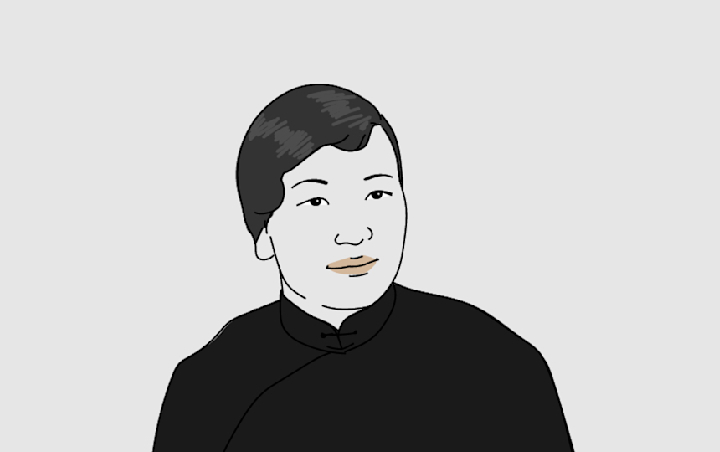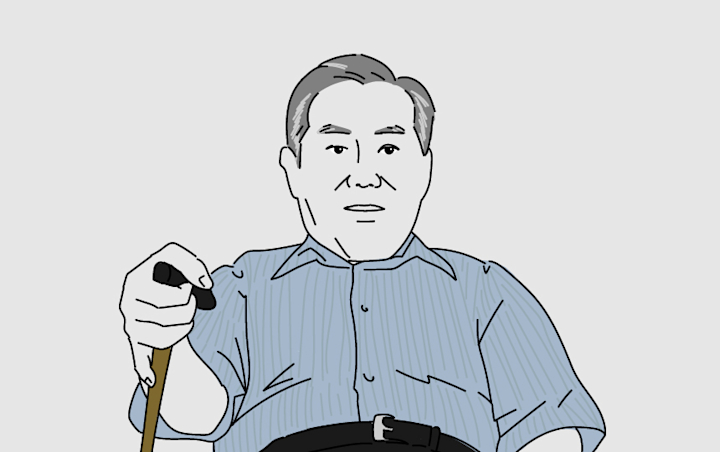左岸文化
2022-04-06發佈
2023-03-06更新
金城武樹的故鄉:池上如何成為大家眼中美麗的池上?|話鹿讀冊

本文出自左岸文化《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結語:想望「地方」的未來〉 二○二○年八至九月間,距離鬧區約兩公 …
金城武樹的故鄉:池上如何成為大家眼中美麗的池上?|話鹿讀冊
本文出自左岸文化《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結語:想望「地方」的未來〉
二○二○年八至九月間,距離鬧區約兩公里的樟香綠廊,也就是池上市街往西走的台二十甲線,路邊橫掛著長長的白布條,大大黑字寫著「無能的代表會配合鄉公所出賣池上」、「池上人不要光電」、「財團滾出池上鄉」。
隨後幾日,街區穿梭一輛小型貨車,不但掛著「光電滾出池上」、「電來了/人沒了」等標語,還用擴音器傳達鄉民反對在鄉境設置太陽能板的立場,甚至揚言要罷免鄉長。與此同時,臉書社群「池上人」也開始出現大量相關討論。台灣近幾年綠能發電的議題,在池上正式浮上檯面。
在這次的太陽能板事件發生之前,光電業者已經在池上尋覓適當土地一段日子了。福文村的這塊農地,地主原本以一公頃每期四萬元租給人種稻,後來有人找上地主,以一公頃每年二十萬,承租二十年。暑假過後,大型機械開始進駐整地,光電業者準備在此種電的消息不脛而走。這個地方剛好在火車站附近,從月台上往西邊望過去特別顯眼,引發的反彈也特別大,前述反對鄉公所與鄉代會的聲浪也因此爆發。
鄉長張堯城於是聯絡縣政府、立法委員、縣議員、鄉代表會、村長等,與地主和光��電業者開會協商,時間訂在九月四日上午十點,地點則在那塊農地旁的馬路邊。由於前一天才正式發出通知,又不是假日,因此原本預定應該只會有五、六十人出席。沒想到,筆者當天不到十點到場,塑膠布棚下的椅子已經坐滿了人,後來湧進的人潮不但站滿整條馬路,甚至外溢到一旁的稻田裡,人數估計在兩百至三百之間。
張堯城一開始就表明支持政府的能源政策,也指出此案已經通過經濟部能源局與縣府主管單位的核准,所以在這塊地種電完全合法。但同時強調這個申請案不需經過鄉公所的同意,鄉公所與鄉代會都是前一陣子才得知這項消息。這個說法後來也得到縣府主管單位與鄉代會主席的證實。
接著,張堯城並未直接反對在此設置太陽能板,但提出兩個層面要地主與業者斟酌,考慮繼續執行種電計畫的必要性:第一,此地附近十多公頃已經通過都市計畫,不久後地目將可變更為建地,預期增值幅度頗大,因此在此種電未必就是最好的投資方式;第二,太陽能發電後,必須在鄰近的馬路上設置電線桿才能將電配送出去販賣,但馬路的土地屬於鄉公所,如果鄉公所堅持不同意電線桿的設置,業者有可能血本無歸。
當天地主並未到場,業者極力說明光電帶來的好處,尤其是對地方的回饋機制,但隨即被發言的群眾一一反駁。兩小時後達成結論,業者主動表示放棄此案,但有一個條件:縣政府與鄉公所協助找到其他合適的地方設置太陽能板,以彌補其損失。
當天到場的鄉民相當多元,除了民宿業者、餐廳老闆、糧商、農民,也有當地的一般民眾,雖然出發點不盡相同,但都一致反對在此地��設置太陽能板。一個月後筆者再度前往現場,機具都已撤離,連原先畫好預計設置太陽能板的白線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同年十一月,經各種行政程序後,業者在舊垃圾掩埋場取得一公頃土地,並於次年三月二十九日正式動工。這次的地點在偏遠的新武呂溪畔,雖然仍有人前往抗議,但人數不多,整起事件因而暫時畫上句點。
這次的風波讓人聯想起二○○四年保存無敵稻景的電線桿事件。儘管時空背景有別,但基本上都是因為當地民眾聯合反對,而成功阻止了某項地方建設。
相隔近二十年的兩次事件,見證了池上人對維護生態環境的共識,即便這種共識並非所有人都一致。觀察池上鄉近二、三十年的變遷,鄉公所的努力功不可沒,但從另一個角度,如果沒有某種在地共識,也不可能成就這樣的發展。筆者認為,「不犧牲環境生態的前提下,首先重視稻米產業為主軸的農業,然後規畫地方的各項發展」的願景。
某個角度來說,已經從一九九○年代開始逐漸在池上形成許多在地人的共識。然而,這樣的共識會持續多久,池上的未來又會如何發展,都有待慢慢觀察。
重新定義「地方」
本書設定以池上鄉為調查單位,一開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多元族群並存是東台灣顯著的現象,但人類學的原住民研究大多以村落為研究地點,筆者先前的研究也不例外。
這樣的做法雖有村落內部資料可較為細緻的優點,但不易具體看到村落與外在生活世界的關係,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也往往各行其是。以池上鄉內十個村落為例,不同族群居住在不同村落,形成大坡村以阿美族為主要人口,客家分布較多的村落是萬安與慶豐兩村,而閩南則在街區的福原村有較高比例。筆者認為,以整個池上鄉(或池上地方社會)為調查單位,更容易看到族群互動的軌跡。
換言之,跳開傳統人類學擅長的村落研究,透過較大空間尺度的鄉鎮層次來觀察,更能同時掌握國家治理與民間動能,了解左右鄉鎮內整體發展的結構性力量,以及其如何與民間動能接合。以這個池上研究為例,早期人口以來自南台灣的平埔族群與阿美族為主,到了日治中期以後,由於官方政策的激勵,漢人急速增加,二戰結束後更是掌握這個地區的主導權。透過歷史過程的爬梳,不但可看出漢人宗教的元宵遶境如何形成並分析其意義,對於諸多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發展(例如平埔族祀壺的興衰、阿美族宗教變遷的軌跡等等),也就更容易被理解,而這樣的視野也更有利於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間的對話。
至於在研究主題方面,社造是本書關注的重點,筆者除了希望補足以往社造研究缺乏與先前地方社會研究成果對話的缺憾,更嘗試以鄉鎮為單位,探索進行社造研究的可能性與意義,而不只是侷限在村落或社區的層次。
自日治時期以來,鄉鎮便是台灣地方行政體系的重要單位,相較於最基層的村(里)與鄰,鄉鎮不但具有法人地位,也有固定的人力編制與經費來源,所以非常適合以之切入討論社造方面議題。
以池上鄉的案例來看,一九九○年代起政府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的確扶持了不少活力十足的社區,例如萬安與大埔;也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成果,例如萬安的稻米原鄉館。然而觀察池上近二、三十年的變化,��大坡池從水泥化工程到國家級濕地、池上米產地認證推動成功、鄉公所推出多項全鄉性社福政策等等,似乎無法光從村落層次的社區總體營造來說明。因此若把「社造」中的「社」定義為「地方社會」,社造可以指稱村落與鄉鎮的營造,很多池上的現象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釋。
相對於台灣西部,池上這樣的東台灣鄉鎮,直到清代光緒年間平埔族人移入前可說無人定居,因而可以較清楚地追溯地方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池上地區自一八三○年代開始有西拉雅系馬卡道平埔族人與恆春系阿美族人定居的紀錄,當時國家力量尚未進入此地區。
一八七五年清廷駐軍後,其他人群才陸續遷入,包括漢人與之後的日本人。日治以後,當代國家治理技術逐步影響池上。二十世紀初期,相當於今日池上鄉境的「新開園區」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單位,此一轄區的劃分,對後來的池上地方發展有頗大影響。亦即轄區面積偏小,地形相對完整,使得池上鄉在地域人群的整合上具有優勢。加上早期居民為了防備來自中央山脈的布農族,不分族群住在海岸山脈西側,也構成許多池上居民共同歷史記憶的一環。
到了一九三○年代末期,在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產業政策下,漢人人口開始超過較早遷入的原住民,而且比例越來越懸殊。於是,漢人成了池上地方社會發展的主導動力。戰後的一九五○年代,每年一度的元宵遶境成為整個池上的重要活動,越到晚近越為重要,連原住民也踴躍參與,而這也成了一九九一年池上首度建醮,並且是由鄉內三大廟(玉清宮、保安宮、池上鄉福德宮)聯合舉辦的基礎。
進一步觀察,十��九世紀末期,池上才開始受到國家力量支配,但日治之後的警察官吏制度、土地登記制度、戶籍登記制度乃至學校教育等,無不使當地居民籠罩在威權統治之下,此一剛開始建立地方社會的移民地區,深深受制於國家政策,其中尤以人口、產業、土地政策最為關鍵。前兩者對於池上的原漢人口比例影響較大,第三者則左右了當地經濟形態與規模,也造成家庭農場的盛行。
一般人或許認為,由於當代國家治理較晚進入,位於邊陲的東台灣可能受到國家的影響較小,但池上的案例卻顯示,國家的宰制力量在此更為顯著。主要是因為,日治初期政府認為東部地區地廣人稀,有利於開發,於是實施一連串的政策,一方面收奪原住民的土地並利用其剩餘勞力,另一方面透過官營或民營等方式,移入外來人口,進行糖業及其他熱帶栽培業。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東台灣引入大量外來人口,並以自行開墾、承租等方式在當地定居,之後在三七五減租、土地放領等政策下,官方的大型事業地轉而由當地居民取得,於是各家庭擁有土地偏少、以小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形態盛行乃成為地方社會一大特徵。而且因為農業是池上的主要產業,碾米廠也因而成為當地最主要的企業體。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家庭不但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人與人間的平等性也得到高度彰顯。
當然,家庭與家庭之間仍會出現貧富的差距,例如經營小商店或碾米廠的通常比較富裕,但這樣的家庭常會透過修橋鋪路、捐助興建學校等行動,一方面展現其善行,另一方面回應可能會被批評「為富不仁」的道德壓力。
他們在廟宇的民俗活動中��也會以不同形式比一般信徒負擔更多經費,例如演平安戲時捐獻較多的戲金、建醮時擔當不同等級的「燈首」之類的。在儀式中認捐更多固然具有「得到更多神明庇佑」的意義,但這樣的行為模式也有財富重分配的意義,可以視為傳統社會中展現共享、共善的一種方式。這樣的文化傳統,至今仍清晰可見。
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使當地民眾早已有了相當於一個鄉的地方認同感,於是奠基於傳統「公」概念的共善與共好,到了一九九○年代之後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從《池上鄉志》的編纂、大坡池的整治,到池上米的認證,我們看到池上鄉民以不同於鄰近鄉鎮的方式投入地方事務,一方面面對新時代的新挑戰,另一方面以超越村落、社區的尺度,善用外部資源來進行社會改造。
最後,在以重視環境生態,並以稻米種植為地方產業主軸的前提下,發展出以鄉公所為單位,進行各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提供鄉民相當優渥的社會福利。這段最近三十年的發展饒富意義,值得仔細討論。
從池上的歷史發展觀察,一九八七年的解嚴顯然具有重要的影響。整體而言,一九九○年代之後,隨著台灣社會的政經發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影響,池上鄉各村於一九九三年起紛紛組成社區發展協會。在官方的經費與觀念引導下,地方動能被激發出來了,並發揮了很好的社區功能。大約也在同一時期,轉型後的救國團池上鄉團委會以及池上社教工作站等團體,以全鄉為活動範圍,經由團康活動、社會教育等方式,為池上帶來新觀念與新想像。
對池上這個正處於轉型階段的保守農村來說,救國團��池上鄉團委會和池上社教站這兩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其意義與全然的民間社團並不相同。救國團池上鄉團委會雖然在一九九○年改制為人民團體,早期政黨運作的組織動員和培訓青年人才等特性,依舊有其作用;而社教站以政府補助經費與社教方針,舉辦涵蓋各年齡層、社群、主題的文教與藝術活動。兩股力量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能,為建立「地方感」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尤其是人才的發掘與培養,間接催生當地志願性社團的成立。
台灣社會推動「社造」,大抵透過「物」的營造,進而達到「人」的改造,池上則略有不同。所謂的「物」是指社區公共事務,大多數從社區綠美化、閒置空間改善再利用為據點,也有部分為在地歷史、文化,一九九○年代如雨後春筍成立的「文史工作室」即是。池上卻是一開始就關注「人」的凝聚和改變,強調全鄉性的生活共同體概念,大坡池的生態保育便是一個實際實踐的案例。
曾旭正在討論一九八○年代起台灣社區尺度的社會集體行動時,將社區行動分成兩大類:一是因應「危機」而產生的社區運動,另一是為「改善環境」而動員起來的社區運動。池上的大坡池保育行動應偏向後者。簡要言之,二○○○年成立的「池潭源流協進會」主要是針對政府過度開發的不滿,「目標在於改良、提升社區的環境品質」,而且倡議者的確大多來自地方上的中產階級。但筆者要強調,若沒有救國團與社教站的觀念啟發,並激起鄉民「愛鄉愛土」的情懷,大坡池的民間種樹活動不易成功,也不可能有鄉公所日後的改弦易轍,政策方向從強調開發轉向重視生態環保。
池上第一次具當代社造意義��的民間自主性結社,與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無直接關連,反而跟救國團與社教工作站影響下的全鄉性動員有關。然而,之後保存無敵稻景的電線桿事件,倒是跟社造政策有關。換言之,是緊鄰此片無敵稻景的萬安社區發展協會試圖發展觀光產業,才有動能去阻止電線桿的設立。當然,若沒有全鄉性的串連與支持,這樣的行動也不會成功。因此筆者認為,必須擴大「社造」的範圍,納入救國團與社教站的影響,亦即池上自一九九○年代起就有兩個層次的社造,如此方能理解池上地方社會發展何以是目前的面貌。
不論是大坡池的保育,還是阻止在稻田間設置電線桿,這些行動的確來自於外來新觀念的啟迪,但池上由於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的因素,早在一九五○年代之後即已孕育出超越村落的地方連結。這種連結在元宵遶境中逐漸形成,並在一九九一年的首度建醮中充分展現,二○○○年之後的社造風潮順利架接在這樣的基礎上,二○○五年池上米認證也是基於此連結才得以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國家治理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有了政府體制的調整。除了池上米認證外,二○○八年開幕的池上日暉國際渡假村,便是在各級政府與民間企業以BOO方式、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國家政策協助下財團進駐池上的例子。從這個角度觀察,影響地方社會深遠的池上米產地認證,其實跟政府加入WTO後有意培植地方競爭力有關,而農委會農糧署推動的稻米產區集團契作,也是在此脈絡下的政策思維。
當然,池上米認證的啟動者來自當地米商,不容否認其有商業利益的考量,但若沒有把部分利潤分享給農友的想��法與做法,亦無法得到地方上具有公信力的池潭源流協進會支持。有趣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原先模糊的「池上地方社會」,越來越向「池上鄉」靠近。
換言之,在大坡池保育與電線桿事件中,參與者雖然會強調「為了我們池上好」、「池上人的整體利益」,其實這裡的「池上」缺乏一個明確的地理界線。但到了池上米認證必須符合WTO精神、以行政區域為單位後,「池上鄉」的重要性益加突顯。以種植稻米的土地位置作為認證依據是其一,以居民的戶籍是否在池上作為發放池上米優惠卡依據是其二。也因此,越到後來,鄉公所在地方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也就是說,進入新自由主義當道的時代,「共好、永續」是許多鄉民的共識,鄉公所一項項再分配的政策出爐,宛如一個「真實的烏托邦」出現在東台灣鄉間。
作者簡介
黃宣衛
花蓮人。英國St Andrews University社會人類學博士,目前為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合聘教授。長期在東台灣做研究,期望以區域研究的視野,跳脫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的分野,從人的創造性與侷限性出發,探討歷史過程中,個人、社會/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