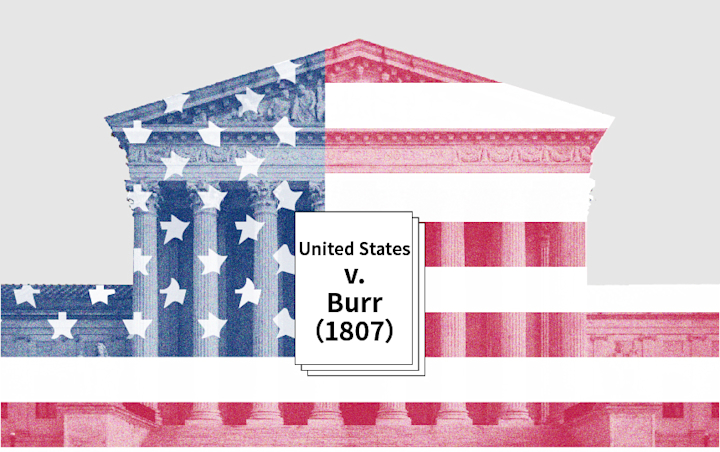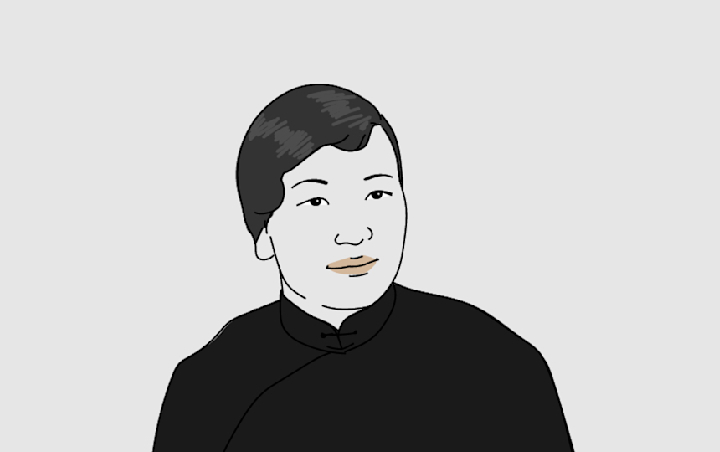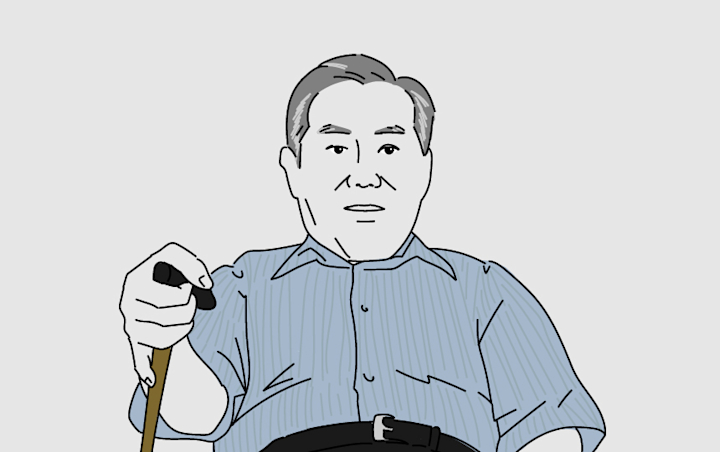天下文化
2018-08-08發佈
2023-03-07更新
《救援:難民與政治智慧的挑戰》書摘:一隻蜜蜂,讓身無分文的難民們重獲新生

難民能為其所居住的國家帶來貢獻、而不是淪為負擔 編按:國際救援委員會領導人、同為難民之子的大衛.米利班德,以自 …
《救援:難民與政治智慧的挑戰》書摘:一隻蜜蜂,讓身無分文的難民們重獲新生
難民能為其所居住的國家帶來貢獻、而不是淪為負擔
編按:國際救援委員會領導人、同為難民之子的大衛.米利班德,以自身經歷在《救援》一書中分享他與組織如何協助難民安置計畫及人道救援行動,讓人們認識到難民危機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應該關心,並告訴我們如何貢獻一己之力去改變。
「難民能為其所居住的國家帶來貢獻、而不是淪為負擔」的想法,是重新思考人道救援意義的基礎。讓我用一個養蜂人的故事,來證明此一論點。
難民們經常說自己在逃跑時,總會帶上身邊最值錢的東西。但對來自敘利亞西南邊德拉省(Dara)的烏雷絲(Um Laith)和阿布.卡拉姆(Abu Karam)來說,這件事卻難如登天,因為他們最珍貴的財產就是蜜蜂,他們從父母手中接下極為成功的養蜂事業。
留下一個兒子在敘利亞完成高中學業的烏雷絲,在抵達約旦時,覺得自己就像是「搭上一條駛向暴風雨的船」。
讓我們工作
現在的她們已經看到一線生機,她們獲得的七百美元,讓她們有機會用約旦的蜜蜂,再次建立事業。卡拉姆先生以害羞、近乎不好意思的表情問我,想不想看看他的蜜蜂。他帶我走出那位於鎮外的家,穿越馬路,來到一個遠離公寓而傾斜的橄欖園。那裡有三個蜂巢,小小的白色木屋,這就是他新生意的起點。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蜂巢,揭開頂端的蓋子,露出自己最珍貴的昆蟲們。牠們是他的未來,經濟和信心的支柱,也是讓他立足於此地�的方法。
當你明白絕大多數的難民其實無法返回家園後,最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他們該如何、且在何地生存,為社會帶來貢獻。對成年的難民來說,最好的答案就是在其所處國家的城市、鄉鎮或農村裡工作。這樣一來,他們能為自己的人生打拚,也能為居住的國家帶來幫助。
然而,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不妨想想西方國家在移民搶走工作機會的議題上,所流露出來的仇視態度。對於中等收入且多有失業問題的國家而言,這個問題影響尤其嚴重。
烏干達讓我們看到了可能性。在二○一六年底,有將近一百萬名的剛果人、南蘇丹人、蒲隆地人和索馬利亞人居住於此。到了二○一七年,南蘇丹人更以平均一天兩千人的速度,湧進烏干達。這些人擁有工作的權利,也可以隨心所欲地前往和居住在任何地方。
他們得到一小塊可以耕作的地;他們可以使用公共服務,讓孩子去公立學校,訓練自己的技能,並透過工作、受僱和貿易的方式,為烏干達的經濟帶來活躍的貢獻。
該國的經濟在南蘇丹人大批湧入的情況下,承受極大的壓力。但一份二○一四年於坎帕拉進行的研究指出,協助難民就業的行為,讓78%的難民不再需要幫助,全國更只有1%的人必須完全依賴援助。作為世界上難民數第五多的國家,烏干達的系統讓我們清楚明白將難民視為具生產力居民的好處。
現在,烏干達被選為測試新「難民問題全面響應框架」(二○一七年由聯合國大會制定,目的為發展全新的難民援助模式)的國家,希望他們的成果能因此更廣為人知。
對難民就業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提供收容難民國額外援助的協議。短時間內湧入大量難民的情況,確實會對經濟造成衝擊。以��約旦為例,其負債對國內生產毛額比例(debt-to-GDP)就從60% 以下,暴增到90% 以上。因此,所有受此影響的國家,將會需要經濟援助。
世界銀行總裁金墉(Jim Yong Kim)關注到此一議題的重要性,從而改變了世界銀行對難民收容國的態度。(過去,中等收入國無法得到世銀的幫助。)他在二○一六年時承諾,會開發新的金融工具如低成本融資和保險產品,協助難民收容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針對中東的情況,其目標為創造二十萬個就業機會給目前滯留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且在接下來的五年內,此區域必須超過一百萬個就業機會。
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抱負——不僅僅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來自更廣泛的國際社會。如果做對了,另一個難題也就有了明確的答案:未來的人道救援不能建立在難民營的基礎上,因其無法為生命帶來滿足。難民營無法讓難民得到安置,更會成為夢想的葬送地。
求求你,給我的孩子一個機會
在流離失所者中,將近半數為孩童。二○一二年,我和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一起拜訪加薩,眾多充滿活力、生氣勃勃和擁有雄心壯志的年輕人,在我心裡留下深刻的印象。無論是世界各地的何處,當你拜訪難民營、非正式住
居(informal settlement)或都市中的家庭時,都會看到許多的孩子。這些孩子的父母總是說著自己對孩子未來的期望,因為他們已經失去對自己人生的期望。
然後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坦桑尼亞鄰近蒲隆地邊界的尼亞魯古蘇難民營裡,我認識了十七歲的費德列克(Frederick)。發生在蒲隆地的內戰,奪走了三十萬條人命。在此地主要道路的一側,是來自剛果的難民,另一側則是蒲隆地難民。
我之所以記得費德列克,是因為他對那可能為他人生帶來改變的事物所抱持的沉重觀點:教育。當時是在一座帳篷裡,他和許多同齡的人坐在長板凳上,面對著我。他有一個黑色的書包。他言詞流利且充滿決心。他說這已經是他第二次
被迫離開蒲隆地,並住進這個「監牢」裡。他說他只需要在蒲隆地再接受一年的教育,就能取得高中文憑。他心裡只有一個問題:「我該去哪裡完成這一年的學業,並得到能被認可的文憑?」我沒有一個好的答案。他與我告別時的話語,深
深埋在我心底:「我祈禱自己的人生不會斷送於此。」
H.G.威爾斯(H. G. Wells)曾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寫道:「人類的歷史愈來愈像是一場教育與災難間的拉力賽。」當時,教育和啟蒙是破壞與災難的取代方案。他的論述放在今日依舊有效。
對流離失所者而言,這是鐵錚錚的事實,因為缺乏有效的教育已經成為一場災難。數據就是最好的證據。在流離失所者之中,有半數的年齡低於十八歲,而在人道救援的總開銷中,僅有不到2%的費用花在教育上。
這會帶來無窮的後患——除了貧困外,還會提高童工、童婚甚至是落入激進主義的風險。他們的父母最明白。如同二○一七年一名在伊拉克的敘利亞難民對我說的,「為了我的孩子,我必須去埃及。就算會死在路途上,我也不在乎。至
少他們能獲得教育。」
神經成像顯示了逆境(如流離失所)會生成怎麼樣的「毒性壓力」6。這也讓培育社交與情緒技能的穩定且安全教育機會,在災難時刻,顯得更重要。因為證據顯示,這種損害是可逆的。
對這些孩童而言,能夠註冊、並接受高品質且足以應付有其他需求的額外學童的當地教育,絕對是最好的解決之道。為了順利進行,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協助,像是語言指導、家教或其�他心理社會活動等。
黎巴嫩創造了「兩輪」制,在此制度下,學校會在下午進行第二輪授課活動。但如果是沒有教育體制的地方呢?或學校能接受的孩童人數已經額滿了呢?儘管黎巴嫩已經非常了不起地讓二十萬名敘利亞學童得已進入學校就讀,但該國至少還有同等數量的學童未能獲得教育機會。歐盟承諾會將教育占人道救援預算
的比例,提高至6%。與當前的水準相比,這將是極大的躍進。但若要改變未來,這必須演化成一股更大規模的全球運動。
就影響力與金錢效益而言,社區本位教育(也稱非正規教育)是彌補國家能力的最好方案。這麼做能將重點放在師生之間的人際互動,而不是建設新學校等各種花錢的設施上。將非正規教育納入綜合性國家政策、並讓這些學校能獲得認證並提供進入正規教育管道的舉措,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地區的主流教育不允許特定的孩童如女孩學習,非正規教育則成為他們的生命線。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