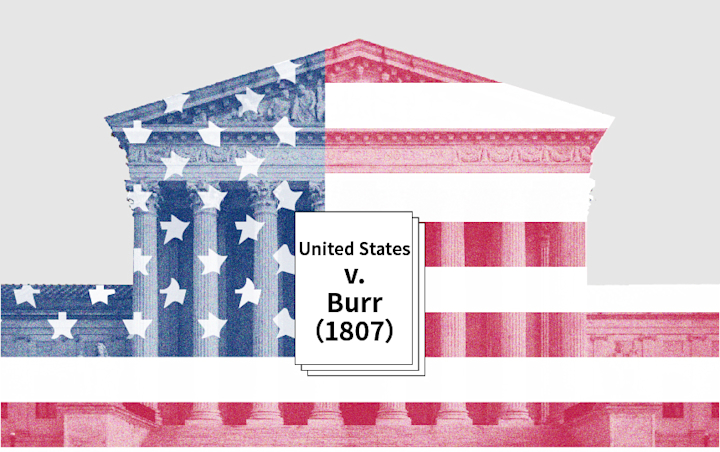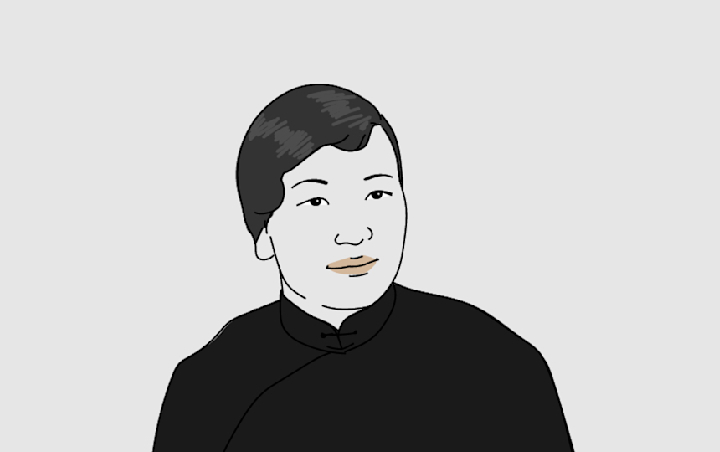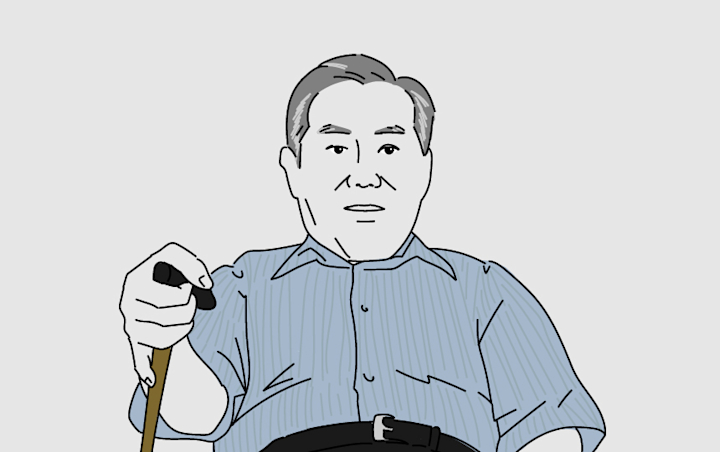商周出版
2018-02-27發佈
2023-03-07更新
《轉型正義》書摘: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

第四章 補償正義 在現代,大部分轉型期政權——無論是在戰後、軍事獨裁亦或共產政權——都採用過某種補償正義的形式 …
《轉型正義》書摘: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
第四章 補償正義
在現代,大部分轉型期政權——無論是在戰後、軍事獨裁亦或共產政權——都採用過某種補償正義的形式。儘管法律文化相異,在此所回顧的實務現況顯示它在各地相當盛行。各個社會是如何考量在補償制度上所作的努力?他們的目的及職責何在?前朝政權錯誤統治的受害者以及社會的轉型期正義又是什麼呢?
接替者政權在輪替時期面臨的第一個兩難,即是新政府是否有義務賠償舊政權過失的受害者。根據國際法規定,任何政府違背其義務皆有明確的法律補救措施。(注1)然而,在全國爭辯如何處置過去惡行的遺緒時,補償正義的議題是接替的政權必須承擔的更複雜的問題,亦會在過去國家的濫權的受害者賠償和國家前瞻性的政治利益之間的矛盾。補償的措施會衍生出在轉型時期特有的前瞻和回顧、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兩難問題。然而不管是平時或是轉型期,補償正義(reparatory justice)由於蘊含著對於從前的過犯的匡正,因而都有向後看的性質。我在本章要闡述的轉型期補償正義,它可以調停轉型期的明顯的兩難,在矯正的目標和轉型的前瞻性目標之間取得平衡。同樣地,轉型期補償正義也可以仲裁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義務,而形成自由化國家的政治認同。
「補償正義」一詞說明了它的多面性,包含許多不同的形式:補償、損害賠償、補救、矯正、復原、賠償金、復權、捐贈。它會回溯古代的前例,這也顯示出轉型期補償正義扮演的繁複角色。轉型期補償的措施會調解�在受害者與民眾、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補救措施,更進一步建構出和巨變時期有關的重新分配的政策基礎。
聖經的賠償條例:〈出埃及記〉
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聖經‧創世記》15:13-14 *
《聖經》對以色列人在埃及時由壓迫到自由的政治轉型,提供了政權輪替的證明和記錄。根據記載,古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近四百年間,遭受奴役與迫害,歷經埃及人多年的奴役後終獲自由,建立獨立的國家,而埃及人亦遭天譴。〈出埃及記〉的故事及埃及人所受的懲罰與災難廣為流傳,但與〈出埃及記〉相關的賠償記載卻鮮為人知。它的隱藏意義顯示政治變動時期的賠償實務一直是高深莫測的。
在《聖經》對補償正義的記載中,以色列人於出埃及的那個決定性的夜晚裡,「向埃及人要了金器銀器和衣裳」。(注2)神指示以色列人奪走埃及人的財物:「以色列人照著摩西的話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銀器,和衣裳。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給他們所要的。他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注3)這段內容暗示財物是埃及人自願給予的,而不是暴力奪取。然而,這段聖經故事卻有各種南轅北轍的詮釋,因為經文既提到「借」和「要求」,也說以色列人「我必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們去的時候就不至於空手而去。但各婦女必向他的鄰舍,並居住在他家裡的女人,要金器銀器和衣裳,好給你們的兒女穿戴。這樣你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注4)
這段記載顯示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間有衣物的交換行為,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暗示著解放的奴隸奪取主人的衣物,現在輪到主人幾乎如奴隸一般赤裸。這個過程可以溯及「賠償」(redress)一詞的出處。「redress」的字源是在公眾場合盛裝打扮,意味著個別不同的地位。在中世紀,這一詞是和衣著、地位和重獲尊嚴有關。埃及人的財富被奪走,與以色列人的「重新穿戴」(re-dressing)的意味更深,它是一種撥亂反正的場景,一種儀式性的重新穿戴,在公眾的見證下恢復其地位。這種賠償方式的古老象徵性,在隨後歷史的許多例子中亦清楚得見。
〈出埃及記〉賠償記載,具有何種新時代的意義?《聖經》的記載支持著一種另類的觀點,財物的奪取,可被詮釋為禮物、借貸、引誘放棄、賄賂、互惠的財產交換。例如埃及人的動產與以色列人離去時所遺留的不動產互易,以補償過去在埃及時經年累月受奴役應得的薪資及其他傷害,甚或是作為賠償的象徵,一種政治地位的恢復。在一種詮釋的版本中,這個故事是關於猶太人利用轉型期的混亂趁隙搶奪被偷走的財物。在另一版本中,這個故事不是指奴隸的脫逃行動,而是神聖計畫的實現。埃及人給予財物是作為賠償,是神意的一部分。(注5)這種詮釋是奠基於《聖經》早先暗示出走的民族將成為「偉大的政治實體」,同時暗示著他們有權主張埃及人的財富。
這個記載有何意義?埃及人的財物被奪取,是否表示太過於回顧既往,被奪去的財物能否作為對於過去奴役和迫害的補償?或者以色列人「重新穿戴」的儀式,意味著展望未來,而被奪取的財物則是建國的資本?《聖經》的內容及爾後的註釋,支持以上兩種觀點。倘若以歷史及政治的觀點闡釋《聖經》對〈出埃及記〉那一夜的記載,其內容就成了轉型期的特殊詮釋學(hermeneutics),轉型期包括了在重大��變故那晚之前長年的奴役,以及爾後《聖經》記載由奴役到建國的轉型期歷史。轉型期的內容既是回顧過去,也是展望未來,這豐富了往後賠償實務的闡釋方式。就我們所看到的,《聖經》的故事有持續不斷的共鳴,因為它以許多例證闡明賠償實務的運作。
戰後賠償及全面戰爭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對德國的索取賠償,曾經引起關於補償正義的意義的疑問。在凡爾賽會議期間,曾針對戰爭責任合計出賠償的條件:依據和平的解決方案,德國須為「全面戰爭罪」負責,並決議德國同意支付龐大的賠償。(注6)在和平解決方案中,發動戰爭的德國,須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卻是以防範為其理由,亦即削弱德國國力,使其無法再行開戰。《凡爾賽條約》追究德國政府的「侵略戰爭」罪行。責任歸屬的協議是集體的,而國際間制裁的衝擊亦由德國政府承擔。經過四年戰爭,同盟國可能會根據其權利請求戰爭的全部費用。然而最後賠償的請求,並非以同盟國「權利」的字眼,而是主張說這是德國的「責任」。
《凡爾賽條約》中所謂戰爭罪的條款,強調德國的全部責任,強迫德國負起「造成所有同盟國損失及損害的責任,……是為其挑起戰爭侵略的結果」。《凡爾賽條約》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同盟及聯盟政府堅持,並經德國接受,德國和其協約國藉侵略而引致之戰爭,對同盟及聯盟政府和人民造成的所有損失及損害,就此結果德國須負起責任。」(注7)根據條約的戰爭罪條款,所有戰爭責任(所有的戰爭費用)將由德國一肩扛起。
《凡爾賽條約》過重的賠償責任引起一些疑問。就如同當時各國所承認的,國際間的制裁太過沉重,以至於引發實際的問題,即德國幾乎不可能償付賠款。(注8)其時國�際經濟制裁手段非常粗糙,不加區別地制裁整個國家。賠償的額度引起了對於賠償的性質與功能的討問:賠償要到什麼程度,才算完整彌補戰爭的罪行?哪些是懲罰性的賠償?《凡爾賽條約》的賠償條款僅有模糊的闡述,這反映出多重目的。戰後條約有意地將責任債務兩個問題分開。全面戰爭罪被壓縮在刑事與民事責任的夾縫間;然而賠償在緊要關頭,卻顯露了民事的性質,《凡爾賽條約》的「全面性戰爭罪愆」條款清楚地區分責任與履行,區分責任與裁判的執行。儘管條約在第二百三十一條對全體債務有所陳述,第二百三十二條亦同時承認資源稀少的問題。雖然同盟國家針對債務範圍及賠償層面的議題爭論不休,條約使用的文字仍顯示其間存有共識,在超過實質損失的賠償部分,德國被要求在道德、政治及法律方面對戰爭負責。不過,同一條約承認德國將不會償付賠款。條約裡兩項約款的獨特措辭,顯示在轉型期的賠償實務有著極大的模糊性。
就像古代的賠償一樣,戰後賠償對這些實務運作的特性及作用,反映出莫衷一是而且錯綜複雜的觀點。而在轉型期展望未來的政治目標時,該觀點亦同時對當前的損害進行補救,以及對過去的錯誤進行制裁,作為對於過去的矯正手段。
「賠償」(Wiedergutmachung and Shilumim)**
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無條件投降,以及戰區的滿目瘡痍,產生了史上最全面的復原計畫,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合計動用了數百億美元。戰後有兩方對德國提出了兩組相當不同的復原請求:其一是戰勝方,其二是最可憐的受害者。在和平談判之初,即便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同盟國已要求德國應賠償它所挑起的不義戰爭的損失。如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規範要求戰敗國支付賠償金給戰勝方�;德國的賠償計畫最初源自戰後的歸還及復原要求。從被佔領的領域至建立主權獨立國家的轉型期間,一九五二年《過渡性條約》(Transitional Treaty)即為重要條文,它規定佔領政權有義務歸還與戰爭相關的財產徵收並賠償其他損失。(注9)
另一個賠償的要求則來自幾百萬集中營的受難者或存活者。在德國及以色列生還者團體達至賠償協議之前所進行的談判記錄,敘述了在轉型期兩個族群的狀況,戰敗國背負著道德破產的感受,而另一方由生還者建立的新國家,亦面臨財政上危機。在德國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譯註1)主持的一連串全面談判後,於一九五二年達成盧森堡協定(Luxembourg Agreements),德國同意支付一筆數目給遭受納粹迫害的受害者代表團體(注10),也同意賠償新建國的以色列。聯邦賠償法(Federal Compensation Law)涵蓋所有受納粹迫害者的賠償,除了賠償身體傷害,若因政治、社會、宗教或理念之故遭到迫害,則對自由、財產、所得、專業與財務的損害進行賠償。(注11)
對受害者及其代表乃至於以色列政府的賠償,並不是根據當時的國際法體系及類似賠償的判例去思考的。或許,最相似之處是傳統的戰後賠償,一九○七年《海牙公約》(The Hague Convention)中的戰爭條款規定,交戰國中違反戰爭規範者須支付賠償。然而,這個觀點意味著接受了德國及以色列為「交戰國」的虛構故事。可是以色列不僅沒有參戰,甚至在戰時也不算是個國家。在一九五二年協定中由西德承諾支付的賠償,如同兩德統一後的協定,迥異於傳統對國家戰爭相關賠償的了解。(注12)賠償指定的受益人並不是戰勝國,而是應負責賠償的國家裡的公民。他們是以色列的未來公民,由受益國代表之。這不是一般戰後的賠��償情形。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賠款一整個改變了賠償的觀念。紐倫堡大審後,國際法有了戲劇化的發展,戰爭相關規範的觸角延伸到國際領域之外,而適用國家內部的衝突。在戰爭末期,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刺激國際人權法的發展,思索在各種武裝衝突中違反人權的賠償問題。(注13)在戰爭法規範下發展出關於凌虐他國受害者的賠償義務,即形成因違反規範而須賠償人民的國家義務。如此會產生一個矛盾的結果:即外國人根據國際法必須承擔的賠償責任,將比本國公民依其國內法體系的責任還要重。根據國際人權法而形成的義務,反而導致接替的政權必須負擔由舊政府的罪行衍生出來的轉型期賠償義務。與戰爭法相關的賠償準則已經演化並超越國際衝突範疇,延伸至國內衝突。
如何能了解德國賠償的方案?「Wiedergutmachung」是德文賠償的名詞,字面意指「重新做好」,亦即回復原來的狀態。(注14)在「肅清納粹主義」(denazifiaction)成效不彰的情形下,賠償是能讓德國在國際社會中重拾信任而獲致政治支持的方式。相形之下,受害者團體不接受賠償能「重修舊好」的想法,希伯來語稱「賠償」為「shilumim」,意指「改過自新並創造和平」。(注15)對受害者而言,賠償是經濟上的補償的必要方式,因此,談判桌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安頓難民們的費用。對加害者及受害者而言,賠償是安頓的費用,只不過各方進行的方式不同罷了。然而,儘管對賠償方案的性質及目的的想法完全不同,若能針對不同的想法進行談判,最後皆能達成政治上的協議。
德國的賠償方案是複雜的轉型期賠償概念的典範。轉型期的賠償實務結合了回顧與前瞻的、道德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正當性。這些或許並非全然如此令人感到驚訝,主要源自戰後及其他轉型期協議中(它們是政治談判與妥協的產物)的賠償條件,而有助於促成各式各樣的、甚或相互矛盾的目的。戰後賠償計畫更顯示出轉型的賠償方案有多重的目的:即謀求個體與集體、受難者與社會的利益。如同我們在其他類似的政治轉型期所看到的,這種多重功能正是轉型期賠償方案的特色。
邪惡的戰爭、失蹤及和解:賠償所扮演的角色**232
在一九八○年代的宏都拉斯,一位年輕人維拉斯奎斯‧羅得里哥(Velásquez-Rodríguez)的失蹤被推測為謀殺的事件,在拉丁美洲掀起連鎖反應,激化出遍及全大陸的賠償政策立場。宏都拉斯法庭表示無法調查該失蹤案,顯然是該國政府所支持的做法,隨後該國即被美洲人權法庭(Inter-America Court)審訊。在一連串重大的判決中,美洲人權法庭認為宏都拉斯已違反《美洲人權公約》(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而宏都拉斯「有責任防止、調查及處罰」公約約束的違反人權事宜。(注16)法庭更認為,無論何時人權被侵害,國家皆有義務確保受害者的賠償。羅得里哥案中無法保障刑事正義的情形,並不只是政府判斷力的問題,而是未能執法以保護重要受害者(公民)的權益損失,促使國際法賠償責任的介入。
羅得里哥案所揭櫫的責任,明確屬於轉型性質,既超越前後期的制度,也是兩者的橋樑。雖然原先的權利和法律同等保護的責任有關,一旦這種預期的權利被廢止,接踵而至的「治療性」(curative)責任(如調查及賠償責任)隨即落在接替的政權身上。羅得里哥案顯示,當調查及賠償責任沒有實現時,違法的狀況可能會繼續,而接替的政權就必須承擔責任。如果說首要的責任,保障,是在展望未來,那麼另外的調查及賠償責任��,就顯得是在追究及回顧過去;因此這些責任可能會無止盡地加諸接替的政權,直至完成為止。(注17)判例法承認的以上責任型態,可以調停新舊政權,在轉型期間擴張人權保護的意義。
羅得里哥案,為賠償責任建立高標準。美洲人權法庭將失蹤記述為「可歸責於宏國嚴重不當行徑所導致的死亡」,並表明政府有責任對因失蹤案而受損害的遺族,給予包括「道德」及「物質」上的賠償。(注18)在羅得里哥案中詳述的高額賠償方案,和拉丁美洲法治文化相去甚遠,該文化缺乏對官方犯行所造成的損害予以賠償的傳統。(注19)
羅得里哥案在轉型期正義的性質上透露了一個新發展,賠償制度對民事及刑事責任,將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基本上,刑事審判後的賠償措施的運用,表示若未就政府重大錯誤加以起訴,將會侵害受害者的權利,並引發相關的政府責任,在接下來的判決亦重申:依據區域人權法規定,特赦法違反受害者的人權。(注20)全拉丁美洲都了解羅得里哥案的意義,當刑事正義無從伸張時,其他的反應可能會接踵而至;法律責任應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而且主要是以賠償的形式進行。
適用羅得里哥案的規範,引發許多疑問。這裡到底蘊含著哪些責任,亦即:在政府平等保護公民的責任,以及恢復這些「權利」的責任之間有什麼關係?更多基本的問題於焉產生:在羅得里哥案所承認的傳統「權利」,是哪一種意義的人權?它們歸屬於誰?以這個觀點來看,平等保護的權利若遭侵犯時,誰會受到傷害,是受害者本身?遺族?而社會是否會因此分裂?當許多國家在特赦舊政權時期的惡行時,這些問題會是政府的免責政策的影響之一。
如果全拉丁美洲皆採行赦免政策,羅得里哥案所透露的訊息聽起來�就顯得太冥頑不靈。經過恐怖的軍事高壓統治、酷刑、死刑及失蹤之後,最終的問題在於接替的政權是否能夠「抹煞」過去,直至煙消雲散?設想該區域統治政權的過去,這樣的政策型態將會顯得特別的頑強乖張。(注21)當智利回歸民主制度時,其脆弱的權利均衡狀態,挑戰著處罰過去軍事政權的可能性,後繼的艾爾文政權遂轉而採取另一種實現正義的形式。如在羅得里哥案中,政府承諾對軍事鎮壓進行官方調查,並賠償相關損害。深入解釋智利的賠償方案,有助於理解刑事與賠償正義間的過渡性關係。政府的「真相及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報告揭露了軍事統治時期數以千計被迫失蹤以及未經司法程序執行死刑的案件。智利總統在代表「真相委員會」向全國人民報告時,將這些罪惡歸於政府的惡行,並將賠償視為「政府坦承報告所詳述的事件與情境並負起責任」。(注22)後繼政權承擔支付賠償的義務,對舊政權的惡行表示負責。儘管最初反對賠償,而且其法治文化中並沒有對政府犯行施以懲罰性賠償的傳統,這種矯正方案在全美洲大陸漸為普遍。在智利之後,阿根廷採行範圍更廣的賠償政策,不僅賠償失蹤案件,更賠償在舊時期統治下的非法拘留案件。(注23)在美洲人權委員會相關的判例中,烏拉圭亦被命令須支付賠償。(注24)
轉型期的判例也重新定義了國家對其公民必須負擔的義務。就像許多轉型期的憲法和刑事制裁釐定國家主權的變化的界線,這些變化也能透過賠償措施加以釐清。轉型期的賠償嘗試彌補受害者,但其在公領域亦有額外的重要性。當賠償是正式接替的政權的一部分政策時,可就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受到損害的狀況去批評舊時期政策的不當。軍事鎮壓的受害者,過去被控��以顛覆政府罪名,國家視其為敵人而消滅之。他們被綁架、施以酷刑、處死而就此消失;他們的孩子被綁架,財產被充公。因此,智利的「真相及復原委員會」建議「道德上」的賠償,「為那些曾被誤控為國家敵人,因而背負污名的死者,公開回復其名譽」。(注25)為了遵守這項命令,艾爾文總統在就職後幾天,在一項公開紀念活動中對智利民眾發表演講,這項活動在智利前軍事統治時期拘禁政治犯的體育場所舉行。在演講中,隨著總統當眾歷數失蹤者的姓名,該姓名便在體育場電子分數看板上亮出來,藉此政府展現對過去惡行的受害者,公開洗刷污名並道歉的誠意。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