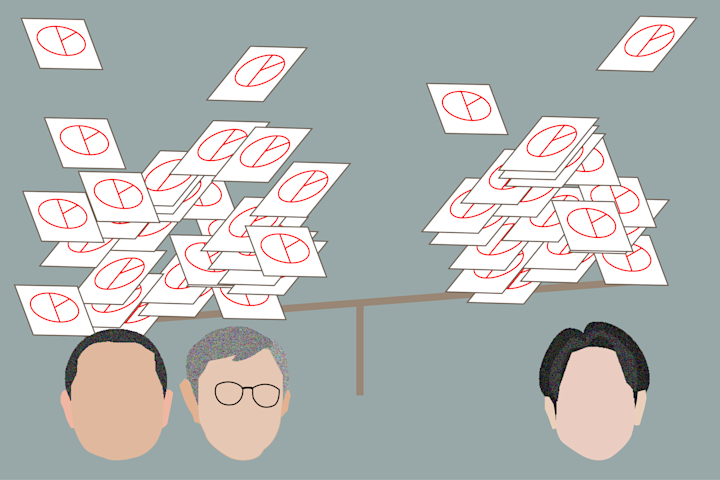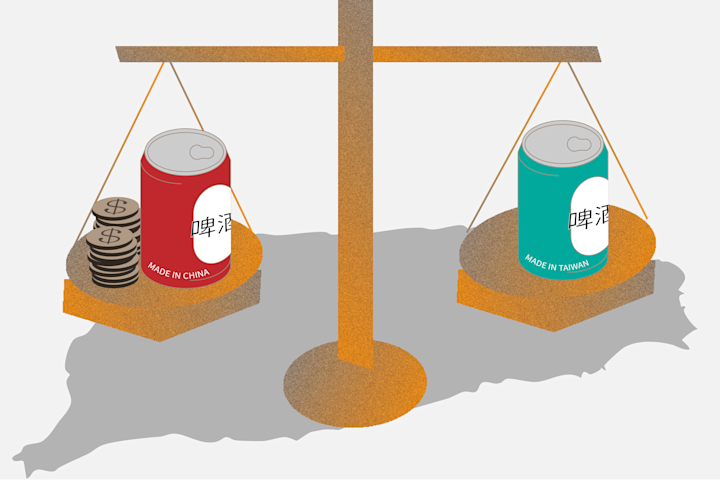法白作者
2022-04-12發佈
2023-04-12更新
妨害性自主罪的迷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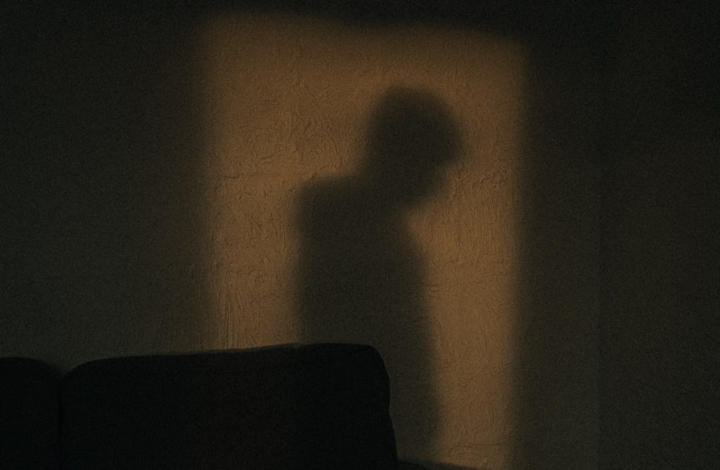
基於被害人被害後的行為反應及驗傷報告等方式認定性侵害犯罪,都容易落入「於性侵害發生後,被害人應該會呈現什麼樣貌」的「典型被害人」的迷思之中,形同強暴迷思的再製,無意間維繫了創造強暴的社會文化。
收聽 Podcast
快速跳轉目錄
以往,未經歷或聽聞強暴的一般民眾,往往會認為強暴案件的發生,是以「黑夜」、「暗巷」、「�陌生人」、「蒙面」、「持刀壓制」等要素構成。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性侵案件被害人都認識加害人,且大多都是被害人熟稔的親人、朋友、老師、同學、同事、伴侶或前伴侶等,未涉及武器的使用,發生地點則多為住宅內等監視攝影機拍攝不到或無目擊證人的空間。
2009 年,法務部針對矯正機關的 3107 名性侵害案件受刑人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其中有 70.8 % 的人與被害人認識,彼此是同居人或男女朋友關係者佔 20.7 %,普通朋友佔 20.6 %,血親與親友子女關係者則分別佔了 8.7 % 及 8.3%,其餘則是網友、部署或同事、同學及其他。
此外,性侵害發生於加害人或被害人家裡的比例就佔了 67.2 %,旅館或飯店與郊外則分別佔了 10.4 % 及 10.0 %。而依據衛福部的統計,2015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性侵害通報案件中,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不認識」的比例僅有約 5 %,彼此關係是「男女朋友」的比例,則從性侵害案件統計開始就穩居第一。
在這些案件中,在實施性侵害時沒有控制被害人的比例佔了 67.9 %,而有實施控制的比例中,又有過半數的人是以「言詞恐嚇」,再來才是「持械脅迫」與「毆打綑綁」等。
換句話說,比起「陌生人性侵」,加害人、被害人雙方彼此認識,且可能已建立了穩定或有情感交流的關係的「熟人性侵」(也稱「約會強暴」),恐怕才是性犯罪的主要類型。
除了雙方彼此熟識之外,學者羅燦煐還歸納出熟人性侵的其他三項特徵,即:
- 加害過程通常較少憑藉武器或暴力,而多憑藉口頭威脅或其他壓力。
- 被害人較少有極力抵抗的跡證,如衣服破裂或身體傷痕等。
- 被害人對於自己的遭遇心存猶疑,而延誤立即報案的時機。
然而熟人性侵往往發生於無監視攝影機及��目擊證人的住宅或房間內,這類性侵案件進入司法刑事程序後,便會面臨犯罪事實欠缺直接證據予以證明的情況,因此如何證明性侵害犯罪事件確實有發生,是法院所需面對的一大難題。
直接證據:被害人供述的取捨困境
被害人對於受害過程的供述,往往是唯一能夠直接指明犯罪事實如何發生的直接證據。
然而,被害人既然指稱自己被加害人的行為所侵害,必然會作出不利於加害人的供述,如果僅憑被害人的供述判斷加害人是否真的有為犯罪行為,便會出現法院判決的事實基礎及對於事實作出的法律評價都被被害人所掌握的情況。
因此,我國法院發展出一套「超法規補強原則」,要求法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不能僅憑被害人供述,還必須存在其他的補強證據,用來補強被害人供述的憑信性,或與被害人供述有相當關聯性,或甚至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
最高法院目前的見解即認為:
「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95 年度台上字第 6017 號刑事判決)
「對立性之證人(如被害人、告訴人)、目的性之證人(如刑法或特別刑法規定得邀減免刑責優惠者)、脆弱性之證人(如易受誘導之幼童)或特殊性之證人(如秘密證人)等,則因其等之陳述虛偽危險性較大,為避免嫁禍他人,除施以具結、交互詰問、對質等預防方法外,尤應認有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始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178 號刑事判決)
歐美國家在過去的司法實務上,也曾認為:如果女性如果沒有在第一時間求救,其對於自己被害過程之供述可信度就會因此打折,必須有更多證據來證明性侵害的真實性,補強被害人的供述。
對此,女性主義法學先驅蘇珊.埃斯特里奇(Susan Estrich)就認為,在普通法的歷史上,對於性侵害案件必須提出補強證據的原則,是基於男性莫名懼怕受到性侵害指控的幻想而來,它的規範核心是出於對於女性證言的不信任。
歐美雖破除補強原則,但實務上仍要求被害人證詞獲得補強
直到 1960 年代,女性主義運動興起,性侵害案件中過於侷限的定義、司法對於被害人證詞的不信任與性經驗的檢驗,以及存在暴力的要求,都一一受到挑戰,其中,也包括針對性侵害案件的補強原則。後來,美國各州不論在立法還是在法院的判決上,都逐漸往不要求提出補強證據的方向調整,檢察官未必需要提出其他證據補強被害人供述的可信度,才可取信於陪審團及法官。
補強原則的破除,意義不在鼓勵法院以被害人供述作為認定有罪的唯一證據,而是考量到性侵害案件的本質困境,避免因為補強證據的缺乏,阻擋被害人提出控訴並進入法院審理的意願與可能性,也是為了避免案件進入法院審理後,即使單靠被害人供述已經足以使陪審團或法官形成被告有從事性侵害行為的確信,仍然因為補強證據的強制要求而無法作出有罪判決。
當時的女性主義者相信,打破補強原則,會讓更多性侵被害人勇於通報案件、現身指控,有效解決性侵害藏著黑數的情況,並將犯罪行為攤在陽光下檢驗。她們也相信,補強證據不再成為證明被告有罪的必要條件,也將有效提升嫌疑人�被起訴、被告被定罪的比例。
然而,後續的實證研究卻顯示,各州在改革性侵害相關法案後,對通報、逮補、起訴及定罪的影響都相當有限。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管理學院教授珍妮.馬什(Jeanne C. Marsh)等人針對密西根州 1974 年性侵害犯罪法立法前後 3 年的每月資料進行比對,發現逮補及定罪率確實有增加,但通報案件卻沒有。
曾任華盛頓法學院院長的陸道逵教授(Wallace D. Loh)也在華盛頓州 1975 年進行性侵害法律改革後,分析西雅圖 1972 年至 1977 年的司法實務狀況,發現檢察官起訴的標準並沒有因此改變,入獄率反而還稍微降低,不過,性侵害佔整體定罪的數量有稍稍增加,也更加重視性犯罪者的矯治。
墨爾本大學犯罪學系教授肯尼斯.波克(Kenneth Polk)則檢視了美國加州 1975 年至 1982 年間的數據,發現性侵害案件在成案率及定罪率上都沒有明顯改變,不過,被逮捕接著被起訴的比例,以及被定罪後的入獄率則有稍微增加。
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刑事司法部教授凱西雅.斯蓬(Cassia Spohn)與茱莉.霍尼(Julie Horney)針對底特律、芝加哥、費城、華盛頓特區、亞特蘭大及休斯頓六大城市進行數據分析及訪談,發現性侵害法律改革並沒有如倡議者想像得有效,定罪率沒有因此增加,而通報率與起訴率也只有在底特律一個城市有所增加而已。
破除補強原則所沒有改變的事情
凱西雅與茱莉認為,破除補強原則所帶來的改變,對司法實務來說是不必要也不重要的。
首先,要求補強證據本來就不是難以跨越的障礙。 曾從事性交行為的身體跡證或一份適當的報告,都能成為補強被害人證詞的證據,也正因為實務對補強證據的解釋相當寬泛,幾乎任何一點點的證據都足以成��為適格的補強證據。實際上,翻閱美國各州法院的判決,你都很難找到一份欠缺任何補強證據,卻認定被告有罪的判決,即使有,也會在被告上訴後翻盤。
1895 年,亞利桑那最高法院在 Curby v. Territory of Arizona 一案中表示,被害人的供述不一定需要被補強證據補強,才足以認定被告有罪,但法官卻在同一份判決中表示,由於「性侵害指控很容易,否證卻很困難」,所以為了避免被告受到有偏見的裁判,被害人必須要有種種行為,才代表性侵害真的發生,最後以本案「證據不足」為由,推翻前審的有罪判決。
後來,也陸續有許多法院援引了 Curby 一案的見解,以此反駁被告對於證據不足的主張,然而,這些判決有的採納了幼童證人的證詞,有的則把被害人向親友求救時,表現出來哭泣、驚恐等情緒反應納入考量,就是沒有一個法院真的單純依據被害人的供述,對被告作出有罪判決。
其次,即便立法宣示補強證據不是判決被告有罪必要的條件,它在司法實務仍然發揮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凱西雅與茱莉訪談的許多檢察官都相信,陪審團不太可能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單憑被害人單方指控,就認定被告確實性侵了他認識的人,換言之,補強證據的有無,也就影響了檢察官是否決定起訴。
如同其中一位亞特蘭大的檢察官所說:「你仍然會因為補強證據的有無勝訴或敗訴。」
即便法律條文有所改變,只要司法體系中的人員欠缺足夠的動機捨棄使用補強證據,那理所當然地,他們仍然會選擇遵循體系中無形的規範,維持既有的行為模式。
國內學者的反思
在國內,也有學者認為法院發展出來的「超法規補強原則」應該被捨棄。
任職高等法院法官的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唐敏寶助理教授認為,《刑事訴訟法》已經規定,法官利用相關證據判決時,必須依循「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不能作出違背常人經驗或邏輯矛盾的判決,而法官要對被告作有罪判決,也必須在檢視相關證據後,達到「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心證程度,實在沒有必要再另外創設一個限制,造成訴訟資源的浪費。
真理大學法律系吳景欽教授也認為,《刑事訴訟法》只有強制規定被告自白必須有補強證據,司法實務透過判決自己建構一套補強法則,已經超出司法、進入立法論的範圍。此外,僅僅因為被害人與被告利害衝突,就認為被害人的供述一定比較不可信,是一種直觀、缺乏實證的論斷。保障被害人供述正確性的關鍵,在於是否有經過被告的對質詰問,發現其不合理或矛盾之處。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李佳玟教授則認為,雖然台灣的補強原則不像歐美國家是針對性侵害案件而來,在證據稀缺的情況下,仍然對性侵被害人造成不利影響,「強暴迷思就在表面中立的證據法則被強化與延續」。
李佳玟教授進一步認為,司法實務對於什麼樣的證據才是合格的補強證據,見解非常歧異、難以統一,與其繼續使用一個不清楚的概念進行判決,不如直接將超法規補強原則廢除,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性侵害案件的處置合理有效。
她提出一套法院處置性侵害案件的方法,區分被害人是否到庭,是否接受被告針對其供述進行詰問,讓被告有攻擊證詞矛盾的機會,來決定需不需要有額外的證據。
如果被害人到庭接受詰問,那麼被告的詰問、《刑法》「偽證罪」對不實證言的追訴,以及法官當庭的觀察,都是避免冤罪的保障機制,此時,除非出現被害人供述矛盾、前後不一等情形,讓法官認為有必要尋找其��他證據予以判斷,否則就算僅有被害人供述能作為證據,只要能讓法官確信被告有對被害人從事性侵害,也能作出有罪判決。
反之,如果被害人因為身心創傷,無法到庭作證,僅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條例》的規定,對特定檢警人員作出陳述,則應該仿照歐洲人權法院的作法,先判斷被害人不出庭有沒有正當理由、有沒有必要使用被害人的審判外陳述,如果是的話,再確認本案是否只有被害人供述作為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決定應該給被告多少衡平措施,例如要求檢察官提出一定程度的證據,或讓被告有機會詰問其他證人等。
但補強原則是為了限制法官自由心證的空間,避免法官僅靠一些可信度不穩定的證言,就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並非針對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而來,一旦允許法官單靠被害人供述就能形成被告有從事性侵害行為的認定,是不是會造成個案法官因為對被告有著先入為主的偏見,提升製造冤案的風險,也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地方。
與被害人相處的相關人士之供述
除了被害人供述外,法院時常以共同生活的家人朋友或頻繁互動的同事師生供述、輔導老師或社福機構訪談紀錄、性平會調查紀錄、醫師驗傷診斷書、PTSD 鑑定及測謊鑑定等證人供述或鑑定人意見作為判斷犯罪事實存否的間接證據。
這裡提及的證人供述,並不是指目擊案發過程的證人,而是指與被害人朝夕相處的相關人士,以及進行諮商、輔導、詢問或治療的專業人員,對於被害人於案發前後反應的相關變化提供說明。
證人供述,一方面被用來形塑被害人的品格、信用及性格,用來確定被害人並無說謊傾向,遇到不好的遭遇通常會以何種方式表現。例如老師作證被害人性格被動消極、自我壓抑,遇到挫折會隱忍、苦吞,家人作證被害人沈默寡言、不擅與人交流,就能合理解釋在性侵害發生後,被害人為何遲遲不尋求援助。
另一方面,證人供述也用來判斷性侵害發生後,被害人是否有異於往常的行為舉止及情緒反應,用來判斷被害人是否遭遇重大挫折。例如父母作證被害人於性侵害發生後,有一段時間變得怯懦、易受驚、憂鬱、沈悶、不願離開房間、具攻擊性、易怒、歇斯底里等異於往常的行為或反應,社工作證於訪談時被害人有類似前述的行為反應。
2016、2017 年間,一名男子藉照顧友人 4 歲女兒的機會,以生殖器猥褻該名女童,後來女童生父接回女兒時,發現其身上有不明傷痕,女童因此交由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安置。
於寄養期間,女童向寄養媽媽主動提到遭受猥褻,並表露出「噁心」與「不好意思」的情緒,寄養媽媽便將此事通報社工人員。社工將女童轉介心理師進行諮商,期間,女童亦對心理師提及遭受猥褻情事,辨認出男子照片時,亦以「生氣」、「提高音量」的反應,向心理師表示:「這是壞叔叔!」心理師因此聯絡社工依法通報案件,法院最終也以寄養媽媽及心理師證詞作為補強證據之一,認定被告確有對女童從事強制猥褻行為。
PTSD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的定義,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指的是經歷、目擊甚至聽聞死亡、重傷或性暴力,而出現四個主要症狀群。例如回憶重現(flashback)、惡夢、接受內外在象徵或暗示時產生強烈苦惱或生理反應等與創傷�有關的「侵入性症狀」,持續逃避與創傷有關刺激的「迴避性症狀」,在創傷後表現出負面情緒及認知的「負面性症狀」,以及發生警覺性及反應性顯著改變的「警覺性症狀」,並持續超過一個月。
必須注意的是,PTSD 未必會在經歷創傷事件後立刻發生,有些人在創傷後一年甚至數年以後才發作,而發作的期間也不一定,PTSD 通常會在發作後慢性化,許多患者在數年後仍有相關症狀,但症狀也可能在創傷後短期內發生,並維持一段相對短期的時間,被稱為「急性壓力症候群(ASD)」。除此之外,就算診斷出患有 PTSD,至多也僅能推論出就診者曾經經歷「創傷事件」,並不能直接推論出就診者曾經「遭受性侵害」。
但有人認為,操作 PTSD 鑑定的醫師並非與受測者日常共同生活的人,鑑定程序仰賴受測者對自身情況的陳述,在這個狀況下,有傾向被害人觀點的可能,而失去鑑定結果的客觀性。就此而言,PTSD 鑑定與被害人陳述似乎會具備同一性,而失去作為補強證據的適格性。
上述女童猥褻案中,法院委託彰化基督教醫院,對該名女童是否有 PTSD 的情形進行鑑定,醫院作成的鑑定報告結果顯示,女童不存在 PTSD 之情。不過,醫院的鑑定報告也提到:「個案雖然並無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但本疾病的形成與否,除了外在事件存在之外,尚需合併考慮當事人的復元能力,因此建議不要以特定診斷之有無,斷定創傷事件是否存在。於鑑定中可見個案對於類似口交的陳述,有抗拒回憶的傾向,且明確表達負面情緒,但必需要花較長時間建立關係,個案才有辦法做更多的陳述。」
驗傷診斷書
驗傷診斷書,包含針對生物跡證所為的基��因分析,以及一般醫學所稱的「理學檢查」。醫師對就診者所為的理學檢查,會判斷就診者的肛門、會陰部、處女膜、內外陰唇是否存在紅腫、壓痛、裂傷或出血的現象,也會注意身體其他部位是否有擦傷、抓傷、挫傷及撞傷。
然而,多數約會強暴的情形不涉及武器或強制力的使用,不易在被害人身上留下明顯的外傷,部分的被害人可能基於驚恐、昏迷等情形無從或不敢反抗,多數的被害人也沒有在性侵害發生後立即報警,錯失驗傷時機,這些因素都導致驗傷診斷未必能忠實顯現被害人是否有被性侵害的跡象。此外,即便驗傷診斷書確實呈現了某些生物跡證或傷痕,也無法透過傷痕推得是何人何事對被害人所為,又即使具備生物跡證,也頂多只能證明加害人曾與被害人從事性交行為,未必代表性行為當下,加害人確實違反被害人意願。
測謊鑑定
測謊鑑定,則是假設人在下意識試圖隱蔽真實時,會產生某些微妙的心理變化,並伴隨身體內部的生理反應,透過監測這些生理反應,用來判斷受測者是否說謊的技術。但人類並不會每次說謊都出現相同的生理反應。
有時,測謊結果會呈現自相矛盾或與其他證據相矛盾的情況,也因此,法院在測謊證據的使用上,往往是在符合既有心證的前提下,才被拿來加強自己的論述,如果與心證相悖,法院也可以以「人的行為與思想無從量化,測謊程序易受個別生理及心理因素影響,而無法如物理、化學試驗般絕對正確」為由,否認測謊結果的矛盾具備影響其心證的證明力。
2020 年,一名男子疑似趁其兒子的女友在客廳沙發睡覺時,用手伸入女子短褲撫摸下體。案件進入法院,被告辯護��人聲請對女子進行測謊,但法院以「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有無必然之因果關係,已有可疑」、「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如已平復,或已合理化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等理由,認為依照相關事證已經足夠認定被告有猥褻犯行,自然沒有對女子為測謊的必要,便駁回辯護人的聲請。
修法能夠解決問題嗎?
1999 年前,我國《刑法》第 221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為強姦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據這項規定,行為人必須對被害人實施一個強制手段,這個強制手段的強度必須達到「使不能抗拒」的程度,並從事姦淫行為,才會構成強制性交。這樣的立法模式,被稱為「強制模式」。
由於這項規定要求必須存在一個「強制手段」,有些人批評,這代表只有被害人作出反抗,而加害人使用壓制被害人的力量從事性交,加害人才有被認定「強制性交」的可能,導致被害人的生命及身體陷入更高的傷害風險。因此,1999 年,這項規定被修正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儘管許多學者認為,條文中保留了強暴、脅迫等文字,代表罪名的成立,仍然必須是加害人先施加了某種強制力,再對被害人從事性交行為,還是維持舊有的「強制模式」。但近年來,法院漸漸認為,只要加害人違反被害人的意願與其從事性交行為,都會成罪,而將這樣的立法模式,稱為「違反意願模式」。
不過,在司法實務上,法官往往會調查相關證據,確定性侵害發生時,被害人是否有做出一定的行為反應,用來推論加害人與被害人從事的性交行為,是否違反了被害人的意願。這樣的司法程序,使得被害人的行為舉止、態度,甚至人格、人際交往,都成為法院檢視的項目,容易形成一股「被害人是否適格」的氛圍,對被害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此外,「不要就是要」、「女人只是羞於表達」等強暴迷思,也導致許多性侵害案件的發生。因此,有人主張,應以法律為工具矯正這種文化,將「違反意願模式」的性侵害立法,轉變為「積極同意模式」。
什麼是積極同意模式
在積極同意模式下,性侵害指的不再是「違反他人意願,與他人從事性交行為」,而是「未取得他人同意,與他人從事性交行為」。兩者差別在於,如果一個人欲與另一人從事性行為時,對方單純的沈默,在前者的規範下,不必然會被處以刑事處罰,因為對方的意願並不明確,但在後者的規範下,就必然會被處罰。
1992 年,加拿大刑法修正,明確採取積極同意模式,規定「同意(Consent)」是指「對參與系爭性活動的自願允諾」,並作出許多具參考價值的判決,可讓我們一窺積極同意模式的實際運作情況。
在加拿大的 P. v. Park 一案中,被告主張在事發前兩週,兩人在被害人裡的公寓裡約會,談論性話題並彼此愛撫,被害人爲被告打手槍(handjob),事發當天,被害人同意被告前往她的公寓,身上僅穿著浴袍在門口歡迎並親吻被告,兩人在數分鐘後從事性行為,而過程中被害人積極參與,因此認為自己應已取得被害人同意發生性行為。
不過,主筆法官 L’Heureux-Dubé 認為,即使被告與被害人在兩個禮拜前從事性活動、討論性話題,被害人當天又穿著浴袍在門口親吻被告,也只能支持被告認為被害人「可能會同意」從事性行為,而不足以指出被害人「確實有同意」。
本於這個邏輯,可以發現一個人所有對於性交行為以外的同意,例如同意進來房間、同意親吻、同意愛撫,甚至同意以性器官進行未接合的觸碰,都不能直接代表他/她同意性交,只有一個人確實同意了性交時,雙方才真正能進行合法的性交。
由此可知,積極同意的立法模式,是為了強化保護個人的性自主決定權,只有在一個人表達出「想要」時,其他人才能合法地與這個人從事性行為。對於欲從事性行為的當事人,積極同意模式課予他們採取明確手段相互確認對方意願的義務,並將那些未能取得同意即從事性行為的人,予以刑事處罰。
對於這種立法模式,臺北大學法律學系蔡聖偉教授認為,在從事性行為前取得對方的明確同意,並不符合一般人的實際生活經驗,有時,是否要從事性行為,當事人間會仰賴曖昧不明的語言或肢體碰觸來試探,如果一律將這種性行為入罪化,不免有刑法過度介入私人生活的疑慮。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廖宜寧助理教授則認為,在目前人際社交規則快速變動的時代,不論是西方國家還是台灣,都尚未建立起一套「性互動的共識」,保留違反同意模式的立法,並在當事人無法表示同意的情形,例外以積極同意模式補充,才能給予抱持一套舊規則的人在性互動上試探的空間,也避免這些人因為在新的性互動中受挫,而引發族群間的仇視與對立。
但李佳玟教授認為,積極同意的取得,不以言語表達同意�為必要,如果從肢體行為中表露出迎合態度,也可以被認為是同意的一種,而且任何一種立法,都在干預私人,重點在於哪種立法模式能夠周延地保護人民的性自主決定權。
至於積極同意模式是否過度保護了願意在性互動上相互試探的人,李佳玟教授則認為,如果彼此間都願意這樣的互動,自然可以選擇「不告發犯罪」來避免刑法過度擴張,積極同意模式的立法,是為了避免那些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在試探中表達反對的人遭受自以為是的性互動。
積極同意模式為「不自證己罪原則」帶來的挑戰
也有人認為,積極同意模式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及「不自證己罪原則」,因為被告可能必須在法庭上試圖證明自己曾經取得性行為對象的同意,如果無法證明或不為任何表示,法官可能會對被告形成不利的心證。
但李佳玟教授強調,無罪推定及不自證己罪的原則並沒有被打破,檢察官仍然必須負擔舉證責任,只是證明的事實,將會從「被告違反被害人意願」,變成「被告未取得被害人同意」而已。
陳又寧律師則認為,積極同意的立法模式,是將法庭攻防上的焦點從被害人在事件發生前後有哪些行為舉動,轉移到被告獲得了哪些資訊,可以認為性行為是合法的。
例如在加拿大 R. v. Goldfinch 一案中,被告與被害人曾約會並同居了 7、8 個月的期間,直到結束這段關係後,兩人仍然會聯絡,並確立彼此是「炮友關係(friends with benefits)」 。
被告表示,當時被害人跟自己說想要來一場「生日性愛(birthday sex)」,當被告將被害人載回住處後,他們與室友一起喝酒、聊天及看電視,被告向被害人表示:「我等等要與你性交(I’m going to fuck you)。」而被害人則回 Goldfinch 以一個微笑,兩人坐在長沙發上、合意接吻,然後兩人發生性行為。然而被害人表示對上開過程已無印象,並主張自己是被被拖入房間強制性交,且被害人主張自己曾表示:「(今晚)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而被告否認有聽到這句話。
在積極同意模式下,被告對於是否取得對方同意的問題上,必須提供相對的資訊。在本案中,「炮友關係」、「電話邀約」與「微笑回應」就是被告用來舉證自己取得被害人同意的手段。
由此可知,積極同意模式雖然在形式上沒有翻轉舉證責任,當時實質上增加了被告舉證的壓力,如果被告事實上是無辜的,他/她還是需要提供屬於辯方的案件理論及證據資料,藉此向法院合理說明自己為何認為在從事性行為前、已經取得了對方的同意。
立法模式的變更,無法改變性侵害案件證據稀缺的問題,但能改變大眾及司法看到被害人的方式
積極同意模式雖然不會造成舉證責任的轉換,但仍然是透過消滅被告的抗辯空間,增加被告在程序中舉證的壓力,來解決性侵害案件在法庭舉證分配上的不平等。
不過,這不代表起訴或定罪性侵害會變得相當輕易,因為被害人遭受性侵害的證據仍然難以保存,也始終難以找到直接證據。
積極同意模式的採取,可能只是為了迫使教育、政策宣傳的第一線動起來,積極宣導取得對方同意才能從事性行為的重要性,以法律引領社會文化的改變,藉此改善性侵害的現況。
2018 年,勵馨基金會舉辦「性別暴力防治與實踐國際研討會」時,邀請瑞典司法院性侵害調查委員會委員安娜.哈奈爾(Anna Hannell)法官分享瑞典在 2017 年修法採取「積極同意模式」��的立法過程。
安娜表示,她不認為積極模式的採取將會提高性侵害案件的起訴率或定罪率,因為舉證的困難度並沒有因此降低。她認為,積極同意的修法,意義在於向大眾傳遞一個正確的觀念及訊息:如果沒有取得對方同意,就不該發生性行為。
應邀參與研討會的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林志潔教授也認為,「違反同意模式」在訴訟上面臨的舉證問題,「積極同意模式」一樣也會遇到,對於定罪率的提高及改變性侵害案件的問題,並不樂觀,只是在程序上往往會轉換用詞,從詢問被害人的視角轉為詢問加害人。
前司法院大法官許玉秀教授進一步指出,定罪率是否提高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透過積極同意模式,改變整個社會的態度與價值觀。
不過,對於積極同意立法的教育功能,有人認為,人們在性互動上的價值觀未必適合動用刑罰來加以「矯正」,畢竟刑事法有「謙抑性」,當法律與文化之間還存在極大的裂縫時,倉促改變制度可能無法得到原本想像的結果。
也有人認為,因為禁止了欠缺同意的性試探,積極同意模式的實際運作可能會與右派合流,導致對於性互動有所遲疑的人,不僅沒有讓自身的性自主決定權隨著個人意志實現,反而因為加重了性的污名化而趨向保守。
【製作團隊】
監製|楊貴智
研究|白廷奕
撰稿|白廷奕、楊貴智
法律白話文運動希望透過多元的形式,幫助人們打開通往理解法律的第一扇門,透過各種可能,一同思辨與關懷,並塑造台灣的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