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柏翰
2015-11-18發佈
2023-05-04更新
「恐怖」的差別與「暴力」的無差別:巴黎恐攻、法軍逆襲與國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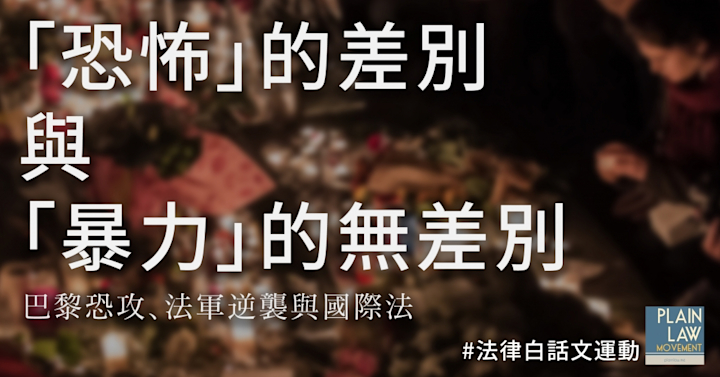
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再度發生一連串的恐怖攻擊,眾人、媒體、各國紛紛感到震憾且恐懼時,還是會在網路上看到一些貌似「理性」但卻混淆視聽的說法。但,我承認每次的恐攻事件都會著實嚇壞我,會一直讓我回想到某次在倫敦地鐵上,看到某節車廂裡有一個被遺留的後背包,然後我只能向不具名的神禱告:它只是一個包包。
「恐怖」的差別與「暴力」的無差別:巴黎恐攻、法軍逆襲與國際法
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再度發生一連串的恐怖攻擊,眾人、媒體、各國紛紛感到震憾且恐懼時,還是會在網路上看到一些貌似「理性」但卻混淆視聽的說法。但,我承認每次的恐攻事件都會著實嚇壞我,會一直讓我回想到某次在倫敦地鐵上,看到某節車廂裡有一個被遺留的後背包,然後我只能向不具名的神禱告:它只是一個包包。
就是這種恐懼讓人草木皆兵,就是那個 against anyone 讓人覺得可怕,不論是誰幹的或在哪裡發生。「武裝衝突」與「恐怖攻擊」之所以不一樣,差別是在於前者強調的是交戰雙方都具有武裝能力(不管是否實力相當),而且擺明了就是要「開戰」,而後者就是一群有武裝能力和戰略的人們針對「平民」發動「為實現其政治目的」而不惜大開殺戒的舉措。
這當中,沒有「誰比誰容易被原諒」或「誰比誰更可憐」的問題。在「武裝衝突」中,罹難者可能被區分為「戰鬥者」和「非戰鬥者」(non-combatant),若被殺害的平民,不論過失(就算被荒謬地視為戰爭所伴隨之犠牲品(collateral damage))或故意,都應該被譴責,甚至是為國際人道法所嚴厲禁止的(先不管執行成效如何,至少建置了一套規範系統,參見《日內瓦公約 1977 年第一附加議定書》)。
然而,「恐怖主義」在國際法評價上根本亂七八糟:你的恐怖份子是我的民族英雄,你的罪犯是我的先知,你的殺人魔是我的聖戰士,這從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於 1937 年制定了第一個反恐公約《防止和懲治恐怖主義公約》,最後卻因未達批准數而死胎可見端倪。
儘管聯合國時代,已經不再以抽象的「恐怖份子」去定義犯罪行為人,而改以禁止並懲罰客觀的行為,針對特定的「恐怖行為」通過了十來個條約予以規範,但在「事實認定」上還是經常落入「定義不能」的政治問題,這終究是出於一場國際政治話語權你爭我奪的戲碼;不過大家也認清了一件事,那就是:嚇壞大家的畢竟不是行為者是何方神聖,而是因為被殲滅的是一群莫名其妙被殺死的平民。
不在戰爭狀態中,卻被平白無故地殺死,才是最讓人惶恐的,而恐怖攻擊的結果也從來不會真的「達到(所謂的)政治目的」,只會激發被攻擊的社會蘊釀另一場報復行動(不論引發另一場戰爭或把矛頭指向「被過份牽連的其他難民」)。當然也會有人主張,那才不是平白無故,因為其中一定有人是支持或「容忍」好戰政權的,所以這樣的報復也只是剛好而已;但,其中難道就不會有反戰的無辜受害者嗎?或與恐攻者來自同一社會,好不容易遠離戰火而逃至其他國家的同胞?
沒有人是特別該死的,任何暴力行為或武裝攻擊的受害者都應該至少「有權利預見自己的傷、亡」,是這份「出其不意」讓人害怕,人們對於天災的發生或許束手無策,只好怨懟上天,但人們對於人禍的反應從來都不會坐視不管,結果只會損及等待邊界開放的尋求庇護者(或許這也是攻擊的目的之一,因為IS從來都不屑那些從戰場上逃走的「異端同胞」),出走中東跟前往歐洲之間產生的巨大緊張,卻不該牽連任何「不相干」或「推論上也許間接相干」的人的自由和安全。
只要害怕死亡的人,都不可能「小看生命」的
「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從來都不是只屬於西方人的,在所有人權位階中,它幾乎佔盡了最核心、最普世、最無疑義的地位,幾乎沒有任何文明、任何社會、任何價值觀的人會主張:「我最渴望恐懼了;我最想要每天活得膽顫心驚了」,這甚至也是 IS 起身反抗西方的原因。若是如此,「武裝衝突」與「恐怖攻擊」所帶來的後果或許無異,因為它們都讓人隨時害怕的要死,但「罹難」對倖存者或普羅大眾的影響卻可能是不一樣的。
在戰時(at war),人們本來就是害怕的,即便心有不甘卻被迫準備死去,不過在平時(in peace),人們本來是恣意的,甚至虛擲光陰的,突然間卻被強拉到死神面前。雖然都是「很倒楣」,但是不該被約分成相同程度的「倒楣」。兩者間的可怕是無法被比較的,沒有誰比誰更可憐,沒有誰比誰不值得同情。
當然,發生在各地的恐怖攻擊是會讓人震驚難過,但未必會動容,而這「物傷其類」的投射,可以從主流媒體渲染的程度發現,比如幾乎同時發生的巴黎和貝魯特恐攻事件,就沒有獲得同等的關注。真如許多人質疑的那樣:「人命不等值嗎?」或許,更好的解讀應該是:雖然都是「他者」,但對於較為熟悉的人事物,勢必就是會比其他較無法引起共鳴的社會來的「更有同感」。
就經驗而言,似乎也真是如此,因為情緒反應與感情上的連結絕對是直接有關的,那種「恐懼」也似乎被理所當然地放大或縮小,這不難理解,因此我才在想「給予歐美較多的感情投射」一定錯了嗎?這樣子的情況,或許很大部分來自「自我他者化」(self-Othering)的想像,再加上對於「惟恐失去安全」的連結,這種投射絕對是複雜且可想像的,但我們或許不能因為包含前者就否定後者在「情緒反應」上的功能和角色。
而這也是我對於「戰時」和「平時」的理解,因為身處相對安逸環境中的台灣人來說,來自後者的衝擊肯定要大許多,但不代表人們對於前者是無感的,只是對於後者的焦慮更多,也不用急於切割或否認,因為那也是無法避免而需要被抒發的情緒。兩者,都該被擔憂、被正視且應對,但應對上本來就可能也可以不同(因為情緒反應有別,這是無法否認的)。
或許平常社會大眾對於戰爭的冷漠讓人汗毛直豎,事不關己的態度可能有很多原因,卻不會是因為「低估生命」,只要害怕死亡的人都不可能小看人命的,只是他/我區分容易使人暫時「擱置」了對其他生命的重視,但也無法因此就認為恐攻可能或可以是召喚平時袖手旁觀的人們關切外在世界的手段。
From Jill Filipovic, Why the Disproportionate Focus on Paris Over Beirut? DOn’t Blame Just “The Media”, Nov. 16, 2015. Photo credit: [Paris] Iakovos Hatzistavrou/AFP/Getty; [Beirut] Joseph Eid/AFP/Getty
對於想用「是一個弱勢對壓榨的反撲」或「是一種被大部分人類逼瘋的反應」等說法來開脫「恐怖主義」的,當然有其真實性與歷史脈絡,但又是另一種��層次且太過美化的「自我他者化」(self-Othering)情況。儘管開宗名義就說明了為何我們最後還是無法定義「恐怖份子」,但那些理由並不會讓他們因此變得不恐怖。
恐怖是沒有差別的,有差別的只是恐懼感,若不區分清楚,就會輕易地劃上理性/不理性、聰明/不聰明、有人性/沒人性、有讀書/沒讀書等分類,可是,硬要否認自己的恐懼也不會顯得比較不害怕,硬要拒絕定義恐怖也不會使它變得不可怕,這才是這幾段想表達的意思。對於經常支持反政府行為(或甚至無政府思想)的左翼知識份子而言,或許一點也不會介意他們的「反撲」,甚至佩服那般敢於戰鬥的勇氣,但重點在於「單挑的對象」。
試想,怎麼不直接衝政府、炸警察局、燒皇官,為什麼挑平民?挑一群隨機、不一定直接壓榨他們的人?如果是跨國界的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像IS那麼強大的(若如他們所宣稱)為什麼不直接「宣戰」?除了迴避人道法的規範外(可以想見其反感,畢竟也是來自歐美光榮戰史的產物),終究,他們在乎的是「創造恐怖」,透過不具針對性而廣泛的無差別攻擊,而不單單是他們宣稱的政治目的,或許有,但幾乎是場無效執行。
說他們被逼「瘋」,其實是在騙自己,因為他們比我們都精明,他們其中甚至許多成員「不得不」比我們享有更多資源、更高學歷、更多人脈、更多身份和訓練。大部分的「恐怖份子」不是「尋求庇護者」,儘管其中可能真有殉道者,但不是出於「絕望」而是「渴望」,他們不是「瘋」,他們是「狂」,是這點讓人遲疑。
不因巴黎重如泰山,更不因巴黎則輕如鴻毛
不由自主「展現大度」的人很多,但那是因為混淆了「恐怖份子」與「難民」的差別,因為你看他們長得差不多、宗教信仰類似,所以延伸你的同情,以及特別慈悲的人道關懷,但該被譴責也或許不是人本身,假若其背後有任何一絲勉強或令人鼻酸的過往沒被看見,但我們對於這個結果也無法不感到震懾。
恐怖份子之所以跟政治異議份子(political dissident)不一樣,因為後者總是找政府開幹,即使手無縛雞之力,然後成為黑名單,而前者專挑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下手,而無法真的解決他們與對手之間的矛盾(除了搏到頭條以外),這也是為什麼兩者在爭取政治庇護(political asylum)或拒絕引渡(non-extradition)兩件事上,總會產生極大差別的評價與效果,不論背後國際操作的因素,後者或許真的感動了世界上某一群人,而前者最後只感動到了他自己。
要真正做到尊重伊斯蘭,就要認真看待向外引發衝突的極端主義者與透過內在修道自我聖戰的基本教義派之間的差異;就像我們決心捍衛佛教徒與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與文化,就更要將之與壓迫羅興雅的僧侶和恐同的教會作出區別。因此,將「受帝國侵略的受害者」與「攻擊處於平時狀態社會的加害者」混為一談,似乎才是更可議、更不厚道的做法。
他們的痛苦需要被瞭解,他們的沉默需要被聽到,他們的需求應被脈絡化;反之,他們似乎也應該想得更多,除了他們殺死的人,以及被他們牽連到的其他正在渡海的同胞、遷入恐怖發生地的朋友、還困在家鄉的親人云云,但他們就直接以「正義」之名幹了這件事,為什麼?因為他們從來都只有想到他們自己,跟他們想挑戰的帝國主義其實並無二致(還巧妙地用虛偽詮釋來包裹神諭),這麼高明,能說他們瘋嗎?
可能出於好意提醒,但每當讀到類似「如果發生在 XXX,你還會在乎嗎?」或「只會同情 XXX 卻看�不到 OOO 的人真是可悲」之類的句型,都會讓人一股火不禁再問:重點真的是巴黎(除了對有親友在那裡定居或旅遊的人而言)嗎?當人們「終於」也注意到中東小巴黎「貝魯特」也發生連環爆炸案時,仍是感到害怕且憤怒的,就像那個令人難以忘懷、伏屍海灘的敘利亞男童。這場惡戰變得「日常生活化」且「去領土化」之際(見哈光甜,《ISIS是 21 世紀的產物,20 世紀的辦法不能對付它》,2015-11-16,端傳媒),這關頭就算用地理(geographicalisation)或文明(civilisation)作為區分他/我的論述來差異化(differentiate)人們對恐怖的情緒反應,聽起來也沒有比較理性的感覺,似乎還是不足以反思「恐怖」。
如果只拿其一與另一比較,那其實是沒有道理的,也不符合「正義」的(雖然,與此同時又可以想像有人批評「選擇性正義」或高唱「文明衝突論」的論調),但我想說的是,既然都是生命,既然都是對安全的威脅、對和平的困擾,就都應該受到大量關注並引發人們的憤怒和哀悼,原因不是因為巴黎多了不起,而是因為殘酷手段所造成的悲劇,在哪都教人害怕,不因巴黎重如泰山,但更不因巴黎而輕如鴻毛。
早已緜延的戰事,霎那間再度一觸即發
然後,才一轉眼,11 月 15 日法國已經開打了,就在總統 Hollande 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關閉邊境,以及美國相應「承諾」將會加緊打擊 IS 之後。法國內政部表示,該國戰機對 IS 在「敘利亞境內」重要據點 Raqqa 發動了空襲;國防部表示,十架戰機共投擲了廿顆炸彈,目標包括一個指揮中心、一個彈藥庫和訓練營等。一切就像隨時就緒,兩天內就集結並發動了「法國在敘利亞境內打擊 IS 中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行動」(引述 BBC 中文網的說法)��。
France has launched air strikes in Raqqa in response to a wave of terror attacks in Paris (Reuters)
姑且先不去看「用暴力譴責暴力」的道德性與有效性的問題,光從其合法性來思考這個行動,試想:如果法軍根本沒有敘國同意,那就算其「宣稱」是為回應巴黎恐攻而針對非國家行為者IS行使「自我防衛」(self-defense,專指涉及軍事武力的手段)的權利是否合於國際法,尤其《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第51條之規定?
依其規定,要件包括:(一)先發生一武裝攻擊(armed attack);(二)先行措施,在安理會採取其他行動前為之;(三)由單一或集體國家發動;(四)應立即向安理會報告。不無疑義的是,IS 這次對巴黎造成的攻擊,是否構成所謂「武裝攻擊」?傳統國際法上,除了「被承認」的交戰團體外,其他行為者是不被視為有能力發動「武裝攻擊」的,充其量只是社會暴動或使公眾脫序的犯罪行為;前者涉及「戰鬥」,後者只是「犯罪」。
所以爭點在:法國如何得以同時以「發動軍事行動」與「調查犯罪事實」回應IS?若視為開戰,那行為人將被視為戰俘還是罪犯?不過這並非本文最關心的事,因為的確有幾項安理會的決議被擴大解釋為「自衛權」得用以針對非國家行為者,而這種主張正好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的強項。
不過,再來細看一下安理會以前是怎麼說的?在 911 事件發生之後,安理會在 2001 年 9 月 12 日緊急召開了臨時會,作出了 1368 號決議,不僅立馬「受理」(seized)了該案件,並確立了「針對恐攻所有『必要』手段」與「符合《聯合國憲章》的『自衛權』行使」之間的正當性,細究其內文,其保護之法益是「國際和平與安全」(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而不是「受攻擊國的主權或社會秩序」喔!這是很有趣的,因為這樣的用語,把單一恐攻事件上升到了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ised),而打擊恐怖主義成了全體國際社會(尤其是安理會自己)的共同責任。
後來,安理會在 9 月 28 日又作出了 1373 號決議,不僅再度確認「打擊恐怖份子」是一項「權利」,也具體提出了各國應該如何「共同對付」恐怖份子的「義務」,更重要的是,這次安理會透過《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即安理會獨享管理國際秩序地位與特權的法律依據)的權力(acting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UN Charter)處置「911 事件」。在決議前言裡,雖提到了打擊恐怖行為應「不遺餘力」(by all means),但有趣的是,在有法律效力的部分,卻只賦予了加強邊界控制、司法調查及凍結資助等手段的正當性(這個區分,可以從動詞是以現在進行式 v-ing 還是現在式 v-es 簡易判斷),而沒有提到可以「使用武力」。
另外,基於安理會的「個案處理原則」,這兩項決議都是針對911事件發出的,是否能被擴大解釋成國際社會針對類似事件的「有效法律實踐」,不無疑問。主要理由包括(一)因為安理會有權處理的都是「被視為影響國際和平」的「政治事件」,而非「法律爭端」,而政治處分不像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判決依據可以有「普遍解釋法律原則」的效力;(二)安理會是由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十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因此只佔世界上不到九分之一的國家,其意見與實踐都不具「普遍代表性」,因此安理會決議通常不被認為具有如「聯大(UN General Assembly)決議」一樣(逐漸)產生立法的效果。所以,針��對巴黎的 1113 事件,若各國(尤其法國)最後逕自援引這些安理會決議,將不具國際法上的正當性?
唔!打到人家家裡去,不用先打聲招呼?
另一個爭點,也是本文更想置疑之處:畢竟被轟炸的IS基地是在敘利亞境內,就算敘國對其失去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也不代表這能因此正當化「侵門踏戶」的非法性,這點從國際法院《剛果對烏干達案》(Congo v. Uganda)中已是確定的見解。在《剛果對烏干達案》中,剛果「邀請」烏干達軍隊幫忙掃蕩叛軍,但後來同意「被撤銷」後,烏國賴著不走即構成「侵略」了;而敘國政府與 IS 之間尚處交戰狀態,因此法軍無從主張「打擊」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或由國家所支持的恐怖主義(state-sponsored terrorism)。事實上,聯合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UN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主席也表示了,國家恐怖主義並非一個國際法律概念,至於若是一個國家實施或支持所謂的恐怖行動,其違反的是國際人權法及武裝衝突法,但仍不賦予他國「武裝反擊」的理由。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delivers a speech at a special congress of the joint upper and lower houses of parliament (National Assembly and Senate) at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near Paris. Photo: Reuters
換句話說,儘管法國在一連串哀歌中風聲鶴戾地橫掃IS,或許在「法式」風格中團結精神(solidarité)的詮釋下,這是一記法蘭西共和(甚至自詡代表整體「反恐文明」)對共同敵人的宣戰與效率,但在國際法的評價中,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為(act of aggression),而非其表面上乍看合理的自我防衛。根據聯大3314號的決議�,只要是由某國家(或一群國家)使用「軍事武力」(use of armed force)影響他國的「主權、領土完整性或政治獨立性」(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就足以構成「侵略行為」(aggression)了。
接下來的日子中,如果安理會只針對恐攻發出決議,卻對法國的反擊不置一詞,那《聯合國憲章》建立起來的後二戰國際法框架(尤以「不(武力)干預」(non-intervention)及「和平解決爭端」(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為特點)就真的徹底被這些常任理事國給玩爛了。不過,私以為,可能還是會想辦法給出「便宜之計」,一如以往,給予一個「可酌參,並無限擴大解釋」的事後背書,而在那之前,還是先用 NATO 集體自救的協議作為後盾。
不過,上個月,俄國才就法軍參戰敘國內戰一事非常感冒,也放話控訴其違法性,因此俄國接下來的動向就很值得追蹤(雖說因為恐攻發生而放它一馬,能交換到的政治條件光想像就很誘人),至於「熱衷反恐」的中國這次當然也是打蛇隨棍上,撥正「齊心協力」的如意算盤。又,搞不好法國後來根本不主張「自衛權」,那事後再來檢討法國總統 Hollande 的發言和作為(比如:法國正處於「戰爭狀態」(at war)),就將令人玩味了,畢竟元首不只是精神領袖,更是國家行為(act of state)之表徵。
最後一個可以觀察的是,美國在這個時候把「反恐領袖」的地位交棒到法國手上有什麼意味?美國的反戰聲浪和明年的選舉?法國國內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外患從來都是解決內憂的最佳良藥,但等不及安內、即攘外的大動作,加上美國馬上「順勢地」應允將「毫不藏私」跟法國分享所有情資,怎麼看,都覺得好像超過 trauma-related reaction了。然而直到作者撰稿時(16 日),目前安�理會除發出「聲明」(statement)讉責恐怖行為外,仍沒有實際決議被「緊急提出」,雖然也有新聞提到「法國要求召開臨時會議」,但英國卻反而傳出「聯合國正在草擬『敘利亞停火計畫』(Syria ceasefire plan)」的消息。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土耳其 Antalya 舉行的 G20 高峰會上特別提到「反恐措施」應當更完備,但應「符合法治」及「確保人權」,這樣的溫馨小提醒背後又有什麼政治意涵呢?這一切實在是太弔詭了,尤其目前法國似乎也沒有要援引《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第五條「集體防衛條款」的意思,但軍事逆襲行動卻已經「炸」開序幕了,到底這些玩弄《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於股掌之間的常任理事國們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將來又打算如何服眾?很值得持續追蹤下去…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