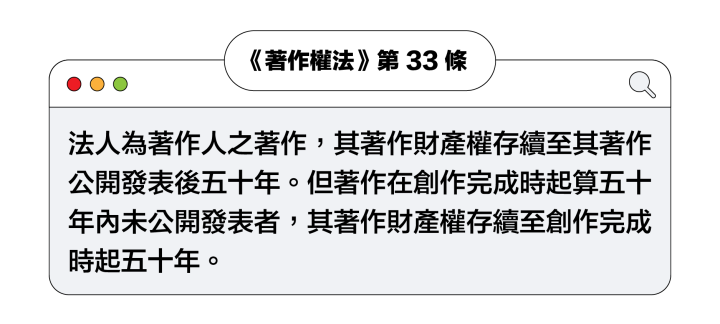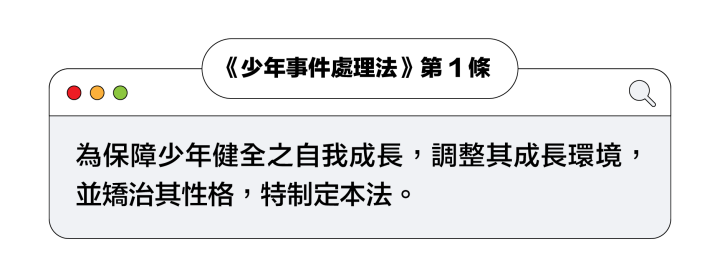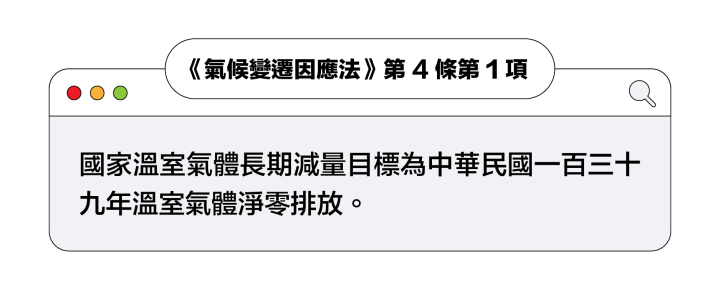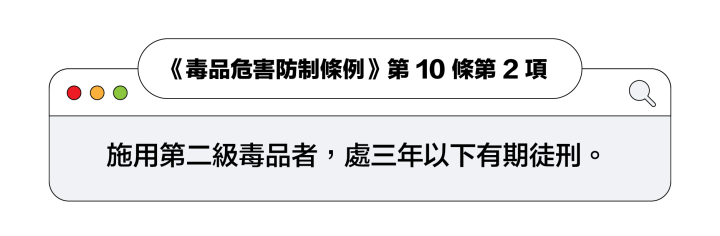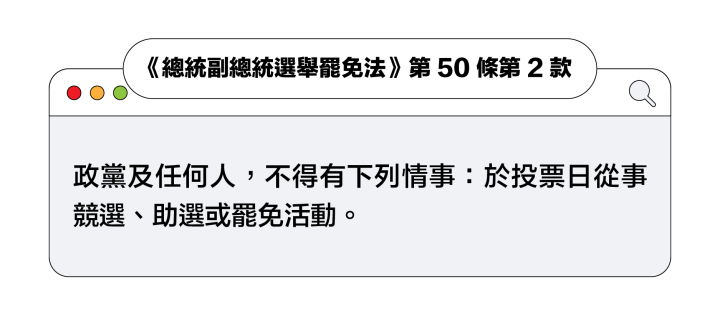WeThinker 微思客
2018-03-09發佈
2022-10-19更新
復仇、正當性與法律: 我們在稱讚什麼?|微思客

白話文編按:對於陝西退伍軍人張扣扣大年三十殺死鄰居為母報仇一案,近日中媒出現兩種不同聲音,讓外界深感案情不單純 …
復仇、正當性與法律: 我們在稱讚什麼?|微思客
白話文編按:對於陝西退伍軍人張扣扣大年三十殺死鄰居為母報仇一案,近日中媒出現兩種不同聲音,讓外界深感案情不單純。不過無論「真相」究竟如何,有無釐清的可能,又或者是否真與中國司法陳腐有關,本文作者是以邏輯推演與法實證主義的立場,來反駁「復仇」的正當性與可訴訟性(即在法律上應該被考慮的情狀與事由)。
作者:若即若離 | 法哲學研習者
前段時間,張扣扣為母殺人案再次刷屏,與之前的辱母殺人案時網友們一片叫好相同,大家忍不住再次為這位「英雄」頌讚歌。

可我們在這件事中,究竟讚賞的是什麼呢?是那種快意恩仇的熱血?是為母復仇的信念?是殺人者不累及無辜的慈悲?亦或兼而有之?
事實上,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這次復仇行動的正義性來源於為母復仇的正當性。但我們按照這種前因後果的邏輯來回溯之前,其母親的死亡似乎同樣不是飛來橫禍,法院最終認定的結果是過失致人死亡,這說明至少法官認為王某當時並無殺人故意。
如此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疑問,難道每一起過失致人死亡的案件中被害人的親屬都可以依此例嗎?你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過失兩個字對行為人主觀責任的減輕讓你猶疑起來。
但更關鍵的是,這時候如果持否定回答,將會面臨著自相矛盾的處境,你無法將你的標準貫徹下去,�同案不同判實乃司法之大忌。所以唯一可能的回答是:是的,這種案件都應當如此,為親人復仇具有天然的正當性。
復仇(尤其是為親人復仇)真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嗎?
復仇的行動在這裡遵循著樸素的報應邏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有因必有果。可笑的是,這種想法所遵循的因果律卻根本不適用這種非物理意義上的事件,我們為親人做出復仇行為的基礎往往在於情感而非遵循邏輯。
可也正是因為情感的不確定性,這種說法下復仇的基礎同樣變得不確定,這無疑將「為親人復仇是正當的」,變成了「為與我感情好的親人復仇是正當的」,這裡的情感因素將使命題徹底情景化,而這種情景化本身便意味著前一個命題的失敗:我們無法在一般意義上認為「為親人復仇是正當的」,雖然後者提高了具體情景中的論證力度。
另一種避開情感討論的闡釋思路是:復仇所遵循的不是簡單的因果律,而是說「如果親人被殺害,你應當為親人復仇」,你的復仇義務產生於事實條件的發生,其正當性則源自於其上位的道德戒律。可問題往往在於,道德命題存在這樣嚴格的層級系統嗎?
就上述的「正當性之鏈結」來看,我個人無法為此一義務尋找到確定無疑的上位規範去論證其正當性,即使真的能夠找到這樣一條正當性之鏈,又如何像法律規範系統一樣去解決無窮回溯的難題呢?如果設想單一的道德命題足以產生道德義務,而無需上位命題去證明其正當性來源,那毫無疑問我們可以藉此產生無數個道德義務,這又是難以令人接受的。
綜上來看,我們所稱讚的復仇似乎並沒有什麼非讓我們接受不可的正當性基礎。事實上,我們所稱讚的往往不是某種合乎正義的行為,其更像是:無論何種行為,只要符合我所接受的固有觀念,那麼它就是值得稱讚的。
復仇具有天然正當性便是這種固有觀念之一。我們的小說、戲劇無不告訴我們復仇是一件值得稱讚之事,更何況為母復仇。但如果在我們從小到大接受的敘事是「復仇是擾亂秩序的惡行」、「復仇帶來的只有混亂」呢?我們現在的固有觀念又會如何?當然,剛才那句話一定程度上是反事實論證,其沒有多少嚴格意義上的論證效力,但我想表明的是:
復仇與正當性之間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強烈的聯繫,它們更像是在一段段敘事中被人為的強行關聯在一起,如果我願意,復仇同樣可以是混亂與無序的代名詞,僅此而已。
若復仇行為正當,即一定正確嗎?
現在,讓我們倒退一步,暫且忘卻上面的論證,假設這樣的殺人行為符合樸素的正當性觀念,那麼,這種殺人行為一定是值得讚頌(正確)的嗎?很顯然,這時候我們心裡多少會有點猶疑,我們也許會認為它是可取的,但未必值得讚頌。
顯然地,本案中一個被我們忽略的事實是:張扣扣殺了三個人,其中只有一人直接與其母親的死亡有關,他擴大了復仇的範圍嗎?王家的孤兒寡母們可以以復仇為理由去做我們所頌揚的張扣扣之事嗎(比如去監獄裡幹掉張扣扣)?
對於前一個問題,復仇的邊界究竟在哪裡?由誰決定這個邊界?很顯然這兩個問題是我們所無法回答的,哪怕同為復仇行為的支持者,也會在這個劃界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但這種細緻的問題確實每一個具體情境中所必須回答的疑問。
對於後一個問題:即使張扣扣的行為符合我們樸素的道德直覺,但很可能他做的是一件錯事。這時候如果像媒體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地去頌揚他的行為,無疑應當頌揚以同�樣理由行為的其它人,比如假設王某的女兒為其父、其爺爺復仇,去監獄裡幹掉了正在服刑的張扣扣。這種假設的故事無疑是反諷的最佳材料:
我們用使英雄成為英雄的理由幹掉了我們造出來的英雄。
遇到這種事,法院該怎麼辦?
最後,我們再退讓一步,即使張扣扣的行為是正確的,法官在判案時需要對此作出回應嗎?
第一種回答:不需要,司法獨立既包括相對於政治干涉的獨立,同樣包括相對於媒體的獨立,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的道德觀念去向司法施壓,否則我們與那些被我們所反對的「干涉司法獨立的人」將沒有區別。司法不應被干涉,無論這種干涉是基於好或壞的理由。
第二種回答還是:不需要,我們的法官在判案時所見的,永遠是依訴訟法證據規則所選擇後的證據,以及其所建構而出的法律事實,這與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媒體所建構的事實,與事情在過去真實的狀態不完全一致。如果說我們連互相看到的是同一個事實都無法確定,如何才能保證不出現「你看著大象,對看見河馬的法官說,嘿,你個傻逼,大象怎麼可能在游泳呢」的情況?
第三種回答依然是:不需要,即使一個行為在道德上是正確的,難道法律上必須要與其道德正確保持一致嗎?如果是這樣,最簡單的反問是:我們還要法律幹什麼?直接依道德判案不就好了嗎?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會依據法律去做出一些不那麼道德正確的判決,否則道德與法律重合之處,將再無法律的存在。

作為一名持實證立場的法學人,接受一種來��自實證法體系之外的標準直接代替法律是難以接受的;但即便拋棄這樣的立場,放棄第三種回答,前兩種回答依舊不受影響,法官依然應當依據他看到的法律事實獨立的判案,至於法官持有何種道德觀念,是不是與非實證立場的人保持道德上的一致,又有誰知道呢?
結論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發現,與江歌(留學生遭兇殺)案、于歡(辱母殺人)案這些案件中折射出來的問題相比,熱點事件中,圍觀的中國人似乎並未長進多少,大家依然憑藉著道德上的正義感對法官司法施加壓力,想要憑此實現心中的正義。
可恰恰是這樣的行為本身,早已讓法律變得不確定起來,這種不確定可以讓人生、讓人死,可以讓既定的規則成為被無視的擺設;每當此時,我都不禁想問一句:你們這樣做與陽光下點蠟燭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法官每當此時必須依據大眾的道德觀念判決,還要法律做什麼呢?
最後,復仇與正當性其實並沒有我們在想像中所構建的那種強聯繫,正義與法律也沒有我們想像中所建構的那種強聯繫,也正是因為沒有這樣強的聯繫,法律的獨立存在成為可能。
至於我們所稱讚的,呵,誰知道我們在稱讚個什麼鬼!?
後記
文章寫完後,網上出現這樣一種聲音「法官是被收買的,案件是被製造的」,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如果法官被收買,案件本身是冤案,那麼文中的推論還會成立嗎?
對於此問題,首先,無論事實怎樣,其實並不影響本文論證的成立,正如本文第二種回答所言,法官本身便未必是因客觀事實所做的判決。
其次,如果你認為這個判決是錯誤的,由誰判斷判決的對錯(對錯的標準問題)將是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很明顯這種判斷是由權威機構做出的。第二,即使判決真的錯了,它仍然應當具有法律效力,判決的效力不依賴於其內容的正確性,而我們只能通過法律規定的程式去改變它。
最後,如果實在放不下這種常見陰謀論的朋友,可以去看刑事實務的律師朋友對卷宗和判決書的解讀,當然,它只能告訴你事實可能如何,在改判或糾錯之前,我們依然應該遵循一個可能是錯誤的判決。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