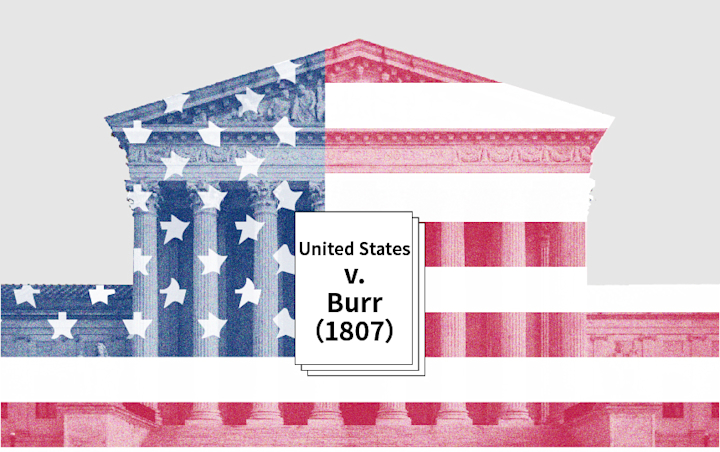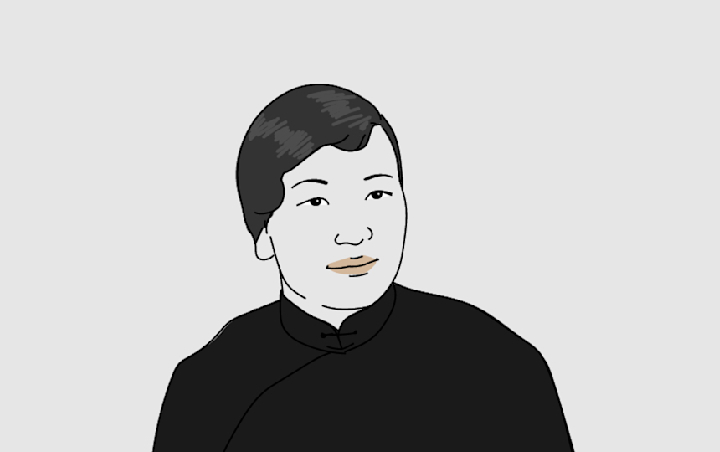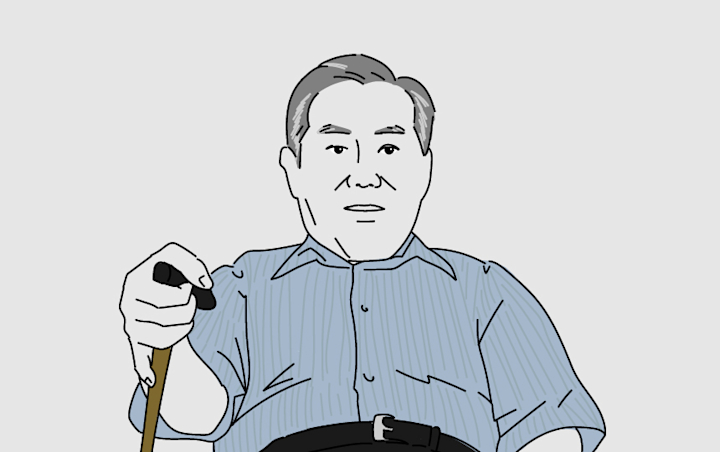李柏翰
2019-07-28發佈
2023-03-02更新
不玩了?要求國家凡事照規矩來的《條約法公約》五十週年|李柏翰

今年是1969年5月23日維也納會議通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50週年。作為「規範所有條約的條約」,條約法公約其實充滿了彈性,因應不斷變遷的國家締約及解約實踐。這篇文章就是要來看看歷史上各國與其他國家分手,深感國際合作沒意思,因此決定透過撤銷條約「不玩了」的眾多案例。
不玩了?要求國家凡事照規矩來的《條約法公約》五十週年|李柏翰
今年是1969年5月23日維也納會議通過《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的50週年。作為「規範所有條約的條約」,條約法公約其實充滿了彈性,除了大原則外(如誠實信用、條約必須遵守、條約解釋方法等),大致上保有相當空間,因應不斷變遷的國家締約及解約實踐。
舉例來說,歹戲拖棚的英國脫歐(“Brexit”)佔據了國際新聞許多版面,弄到最後已經不只是英國內部的政治問題,也是條約法的問題:比如英國是否可以單方依《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規定脫歐?由於這是該條約生效以來,脫歐規定第一次被啟動,因此不管是英國或歐盟都在瞎子摸象,琢磨要如何進行。
另一方面,更深一層來說,當全世界都把歐盟視為區域整合最高境界的一種典範——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sation)——這起「脫歐事件」更是當代國際組織正當性的嚴峻考驗。這篇文章就是要來看看歷史上各國與其他國家分手,深感國際合作沒意思,因此決定透過撤銷條約「不玩了」的眾多案例。
最糗的,莫過於國際聯盟
事實上,自一戰以降,國家脫離國際組織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比如第一次的“Brexit”是1926年6月巴西片面宣布脫離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緊接著在1930年代,原本雄心壯志的國聯氣數已盡,拉美國家率先發難紛紛脫離這個一度風光的世界性組織,而軸心國(德義日)更不用說了,老早就不想玩了。
這應該是國際史上最大規模的解約潮,而國聯的後繼無力,對企圖透過「條約建立之國際組織」來促進世界和平、國際安全、國際發展倡議者來說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象徵了「(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重大挫敗,也成了強調權力平衡、比拳頭大小的現實政治最有力的經驗證據之一。
因此,從國際關係或國際法的角度來看,脫歐不只是個單一面向的事件。除了英國脫離歐盟以外,歐盟更因此失去一個重要成員,其影響是深遠且多面的:英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將不再存有「締約國」彼此之間的單一法律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多條不均等發展的雙邊關係,這顯然會對歐洲政經局勢造成不小動盪。
離家出走,為求博弈籌碼
二戰後,大國其實仍蠻常利用「離家出走」來要脅國際組織的。1977年美國離開國際勞工組織(ILO),因為ILO在1975年大會上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觀察員資格。1980年美國強勢回歸,原本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ILO,竟接受了強調自由市場競爭的「華盛頓共識」,轉為注重就業與薪資不平等等問題。
1984到1985年間,英、美、新加坡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經營不善」,相繼決定退出,重創原本就財政困難的UNESCO。
雖然後來又重新加入,但�因UNESCO大會在2011年通過了巴勒斯坦「會員國資格」的提案,美國及以色列在2017年又祭出「退出通知」(2019年元旦,解約正式生效)。
2016年蒲隆地、南非、甘比亞等非洲國家揚言退出國際刑事法院(ICC),出於對「傾向起訴非洲領導人」這潛藏種族歧視的司法系統之不信任,為象徵中立、正義、人道的ICC蒙上陰影。懷疑主義當道,美國也在川普當選沒多久,就在2017年宣布退出好不容易在2015年談判成功的《巴黎(減碳)協定》。
脫美脫非脫歐,通通脫掉
上面都是所謂「專門性國際組織」被認為過度涉入政治,讓國家有不爽的正當性而出走。惟1984年,因非洲統一組織(OAU,於2002年改為非洲聯盟)內部分歧,多數決承認了西撒哈拉的主權會員國身份,摩洛哥怒退OAU,險些使原本就高度政治的「非洲團結夢」破局;直到2017年摩洛哥才又重回非盟懷抱。
類似情況還包括2017年委內瑞拉啟動的「脱美」計畫,其於2019年4月下旬完成所有條約程序,正式退出美洲國家組織(OAS)。這當然與美國和OAS經常眉來眼去,讓委國當局不堪其擾有關;若把這件事連結到委國後來爆發的「政變」,則不難想像川普政府與OAS幾乎同步承認新總統這件事,多麼耐人尋味。
本來就不是歐盟會員國的瑞士,前陣子因為在歐洲人權法院中敗訴,國內也出現了退出《歐洲人權公約》的聲音。而這幾年歐洲各國大選中,都能聽聞極右政黨提出「脫歐」等國家主義式的政見(甚至是創始國之一的法國),而且其實都不乏有民眾支持;這似乎顯示歐洲式的多元整合路徑也遭逢嚴厲的挑戰。
要馬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或許我們還能這麼診斷:英國脫歐,其實是國際社會早已發生質變,國際組織舊有的正當性受到質疑的症狀之集大成。後冷戰的國際社會逐漸多極化(multi-polarisation),各國越來越倚賴多邊條約建立起的國家組織,來因應全球化伴隨的種種問題。這也使得後來的條約越訂越細緻,國際組織越來越專業分工。
這趨勢沒有必然不好,但姑且先不談一百多個會員湊在一起「共識決」是一件耗時且沒效率的事,幾乎任何議程都難以真正促進相互理解。大幅增加的溝通、談判、行政、人事成本,讓所有國際組織的秘書處都遭受學者的批判、政府的攻擊,動不動就面臨拒繳會費、拒絕出席會議,甚至揚言退出組織等威脅。
這裡出現一個弔詭的情況。全世界不同部門都提高了對國際組織的期待:公部門要它以會員國最佳利益為主,私部門要它對贊助者負責,第三部門把它想像成社運的最高場域,於是許多組織就在尋找新定位、維持正當性的路上充滿迷惘。幾乎所有組織都在談「不拋下任何人」,卻不知道方舟�究竟應該帶上誰。
結論
開頭提到今年是《維也納條約法公約》50週年,卻一直在談各方透過「解約」方式退出國際組織;乍看之下,好像我在貶低條約的崇高地位,但事實上,這些故事反倒突顯了,正是因為條約制度所強調的「自由意志」(free will)與「自願性」(voluntariness),才使得條約成為舉世承認的主要法源之一。
反之,也正是因為國際組織本身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化,反而與條約制度產生拉扯。從傳統上只需依賴國家自願締約「加入」,就足以取得法律與政治上的正當性;到現在國際組織已經不再圍繞著「主權至上」的原則打轉,許多其他並列的價值正挑戰著「以條約為主」的治理內涵,比如民主、人權、永續發展等。
由此出發來看後冷戰的國際社會,就會發現當今國際組織已不純粹是國與國「透過條約」針對某個目標約定權利義務那麼簡單。組織一旦成立,它就會在其所處的時代中逐漸形成自我的意志與能力,進而在締約國互動時,與各國發生「類似法律關係的關係」,而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會大量出現國家組織主體性的討論。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